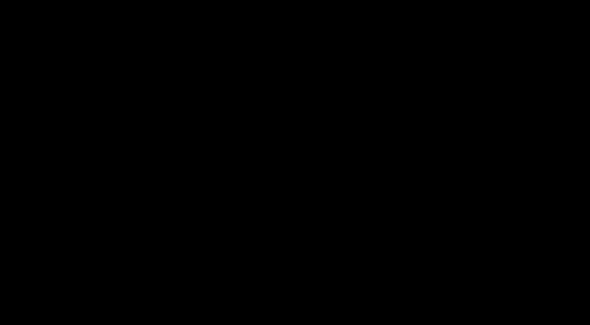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的王力,不久前因病去世。在去世的前几年,王力重新于某些公开场合露面,发表过一些讲话,写过一些文章。九三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力的一本回忆录 。这本书对我们了解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了解王力本人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为什么权倾一时?为什么大起大落?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其他几个共产党理论家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照说,这几个秀才在党内的地位本来并不高,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可是在文革发动后短短几个月间,他们一跃而居于权势的顶端,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名声,包括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内阁重臣和封疆大吏们还要大得多。
这种情况是文革前十七年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它看来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那么,意识形态的专家们理当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统治本来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传统形式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支配着世俗的权力。整个社会明确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谁被赋予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的角色,谁就成了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最高法官。
换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亲自任命,由精通经典的教士而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种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论的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从表面上看,这更符合、而不是更不符合当时广大革命信徒所想像的理想国。
具体说来,王力等人在文革中的权力表现在,他们可以宣布什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什么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什么是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什么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高度政教合一的当时,这样的一句话就有生杀予夺的无比威力。
不言而喻,王力们的这种权力是毛泽东赋予的。一旦毛泽东不再承认他们的讲话代表了毛的路线,一旦他们不再被认为是毛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们的权力顷刻之间便化为乌有。
在这一点上,中央文革这批秀才们和其他共产党干部的情况大不相同。其他干部或多或少是允许“犯错误”的,唯独中央文革的成员们不行。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被视为毛路线的权威解释者,这种事如何能打折扣?要是人们发现中央文革成员的讲话也是可对可错,也是可能符合毛路线或可能不符合毛路线,因而可遵从可不遵从甚至可造反,这个权威解释者的解释就没有权威了。一般的书有点差错,还可以继续发行继续使用。唯独字典不行。字典一有错,就必须收回重印。
是故,一旦某个中央文革的成员被判定是“犯了错误”,准确地说,一旦毛本人感到有必要对某一中央文革成员的某一行为加以公开的纠正,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立即打倒,当下清除。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其他的中央文革成员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权威地位,从而继续发挥他们原有的政治功能。
打倒王力之谜
《现场历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打倒王力之谜”。
众所周知,王力是在六七年八月底被打倒的;应该说是从那时消失的,因为在当时,中央的报刊,中央的文件,也包括中央首长的讲话都不曾提到王力被打倒一事。我们只是从群众组织贴出的北京动态的大字报上获知王力已经垮台,据说主要错误有两条,一是杂志社论,其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给这篇社论批上“毁我长城”,“大毒草”;一是八月七日在外交部的讲话,其中提到“夺外交部的权”,毛泽东把这篇讲话也批为“大毒草”。
可是按照王力自己的记叙,事情却完全两样。王力坚称他被打倒的真实原因是他得罪了江青。
至于前述两条错误,王力辩解道,第一,他并“不知道有‘军内一小撮’这个词”(该书第74页)。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王力这时因为腿被打断,请了假,没有工作,这个时期的宣传工作不是王力管的。这时报上出现了一系列‘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这同王力无关”(第74页)。王力非但不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而且还是“一直反对江青康生等人对部队的一些做法”,“是‘保卫长城’的”(第10页)。
第二,关于八・七讲话,王力说,他“没有系统地发表什么讲话,只有一些插话”(第10页)。是别人把它整理成所谓八・七讲话,而“有些重要内容他们没有整理进去”(例如支持周总理的话)。王力声明,他的插话“是根据毛主席的调子讲的。差不多是主席的原话”(第10页)。譬如“打倒陈毅”的口号,毛说过:“群众喊打倒就让他们喊嘛!”(第10页)再有红卫兵办外交的话,“我不是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我是说:‘能处理红卫兵问题的人就能办外交。’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第61页)还有“有点权才有威风”一话,“这不是我的话,毛主席讲过,林彪也讲过”(第62页)。
说到夺外交部的权一事,王力解释道,“外交部夺权是一月十八日就发生了,成立了监督小组。怎么能说八月七日才由王力号召夺权呢?”“八月普遍要建立领导班子,这也不是王力号召的。这是毛主席的意图。”(第56页)王力表示,八・七讲话以前,“我从来没有插手外交部的事”(第55页),八・七讲话以后,“外交部搞了个领导班子的名单,要我批,我退还给他们,我说外交部是总理管的,请你们送总理”(第56页)。因此,“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八月七日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这个根本不对”(第55页)。最后,王力还说,毛主席“早已看过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讲话中那些过分的话,就是他的原话”(第64页)。
王力的叙述和我们当年获知的有关情况相去甚远。不过细细想来,也许它们正好互相补充。事情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不论是搞乱军队还是搞乱外交部,主要责任实际上都不在王力。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社论和八・七讲话,要么与王力无关,要么王力只是奉旨行事。问题在于,毛泽东自己后来变了主意。毛想稳住军队,稳住外交。这样,毛就必须对前阶段的运动来一个转折。这就需要给外界一个交代。这就需要抛出替罪羊。既然江青早就对王力不满,此刻正好嫁祸王力,这样,王力就成了牺牲品。
根据王力的记叙,江青曾向毛说:“王力以为七・二零以后天下不是毛泽东的了,是他王力的了。”毛说“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江青和康生便证明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于是毛“才同意先把王力打倒一下再说”(第65页)。
假如这段记叙不错,我们很可以推断,毛同意打倒王力,其实并非误信了江、康的谗言;当毛说“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时,那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暗示,那就是要江、康在王力的历史和身份上作文章。毕竟,毛自己知道王力的讲话无非是传达他的意思,因此若以此为罪名将王力打倒,纵然一时间骗得了一般群众,终究还是会被人们识破其奸诈;所以毛需要给王力再加上别的罪名。
直到写这本回忆录时,王力还认定打倒王力是江青、康生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欺骗了毛主席,殊不知那正是毛主席自己的掩耳盗铃。或许王力心里是明白的,但他宁可把一切推到江青和康生头上。
关于“二月逆流”
六七年的二月逆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有关二月逆流的内幕却始终不清不楚。以往我们知道的情况无非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大闹怀仁堂,无非是全国许多地区由军队出面镇压造反派。这中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疑问。第一,那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向文革派发起主动进攻?第二,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那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有那么大的权力吗?
王力的回忆录给这些疑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原来所谓二月逆流,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据王力透露,“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就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第29页)。“这次会上,毛主席作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对陈、江错误问题,只准在他这里和文革小组会上讲,不准在别的场合讲。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和叶群。”(第29-30页)
这次会搞得陈伯达很紧张,下来对王力说他要自杀,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连康生也大骂“都是江青搞的”(第30页)。接下来二月十四日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江青借口病了,不参加。可见当时的气氛。如此看来,在两天之后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开炮批评文革派,甚至批评文革,那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另外,我们早就知道,在二月八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就讲过,冲击军队大院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坏人”,并劝告军队在受到冲击时“首先向进攻者退避三舍”。这话很容易让军队理解为,如果造反派继续冲击,他们便可以回敬。二月逆流的成因,大抵如此。
王力指出,在文革中,毛泽东主要是反右,但其中也多次提出反左。“可是他的特点,每次都以反左开始,以反右告终。表现在二月更清楚。是谁先反左?是毛泽东,不是几位副总理和元帅。是毛泽东先提出要批评陈伯达、批评江青。二月十日就提得很尖锐了。然后才有几位副总理和元帅顺着主席的反左反下来了,结果没反几下,马上变成反右,变成‘反对反革命逆流’了”(第50页)。
迫害与愚忠
王力被打倒后,在秦城监狱关了整整十四年(1968.1.26–1982.1.18)。王力说在秦城受到的迫害和虐待“是最惨无人道的”。“特别是头五年,五年不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包括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一个人从门上的小洞里看着王力。五年睡觉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洞”白天只能坐在木板上,还必须坐在一定的位置。“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极少的水喝”。“足十年,家里不知道王力是死是活,人在何方”(第14页)。
王力关进秦城,从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也从未受过审讯。王力说“毛主席不许专案组审讯王力”(第14页)。为什么不审讯?怕的是泄露天机。替罪羊的命运就是被封口的命运,当替罪羊就是要你吃哑巴亏。王力垮台后的最初几天,群众贴出不少揭发批判王力的大字报,周总理下令不许贴,贴了的要覆盖,王力的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的群众组织来搞。这也是怕群众起来一搞,不小心捅破了那张纸,暴露了真相。
王力还写到:“特别残酷的是,江青他们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用喇叭放噪音,不给看病,还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你造成幻听幻视。我还记得,有一次喇叭里,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反复广播。我憋了三小时,最后高呼:‘王力从小就是共产党!现在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据最高指示,王力宣布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我拥护枪毙王力,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个牺牲是必要的。’我反复高呼三遍,然后就走向刑场。一天在喇叭里宣布枪毙多少次,每次宣布枪毙,王力就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唱国际歌。然后又宣布不枪毙了。”(第14页)
读到以上描述,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共产党的内斗不但残酷无比,而且下流万分。王力的遭遇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王力高呼,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拥护枪毙王力”。这使人想起科斯特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书中写到一个老共产党人,被领袖诬为反革命,起初他还竭力为自己辨诬,后来他却违心地认了罪,因为他说服自己,只有承认党强加给自己的罪名才能维护党的威信。
乍一看去,王力的表现可谓愚忠之极;但也不尽然。以王力当时的处境,他不作出如此愚忠的姿态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他表示抗议,表示不服,其后果难道不是很可能更糟糕吗?在不忠不行的情况下,无所谓忠;做出忠的姿态,未必是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算是对共产暴政下出现的大量所谓愚忠现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难以承受的荒诞
在这本回忆录中,王力再三强调,他坚信他这一生选择的道路,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正确的”,他“是死而无悔的”(第78页、第191页)。
就在王力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国际共产阵营已经土崩瓦解;中国虽然还维持着共产国家的躯壳,但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并且失去了人心。所谓“正确”,所谓“死而无悔”,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大话而已。要说这些大话还包含了什么信息,那就是王力执意维护自己、维护自己一生活动的意义、维护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强烈愿望。
王力说:“我这一生,除去在家里生活的短暂时间以外,从十四岁开始,就是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之中。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工作的、战斗的。文的、武的、地下的、地上的工作都作过。从最低层的普通战士,到宝塔的尖端,最高的领导层,都经历过。我是被捧上了天,又被摔到了十八层地狱,从中央领导人,一下子被送到秦城监狱去当囚犯。”(第158页)--这说的都是实情。
从这段不无炫耀的自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王力的整个一生,尤其是他一度享有的巨大荣耀,都是和中共联系在一起的;否定中共无异于否定自己,所以王力要执意为中共辩护,因为那也是为自己辩护。
不错,王力也受过很大的苦,让这个制度折腾得九死一生。不过受苦要看为什么受苦。王力是被当作替罪羊而关监狱,那既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又不是为了真理而作出光荣的牺牲。这样的受苦是最缺少意义的,因此也是受苦者最想找出一种什么意义来宽慰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深受无谓之苦的人,反而越是爱对外宣称“无怨无悔”。否则,那种赤裸裸的荒诞感未免就太难以承受了。
不管王力怎样费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永远对共产革命事业充满坚定信心的胸怀宽广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可怜的灵魂。
1996年12月
(看中国:http://kzg.io/gb3k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