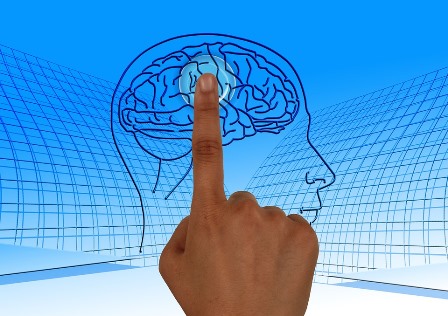文革前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接见时传祥,有一段流传极广的讲话:“我当国家主席做领导工作,你当工人做掏粪工作,我们工作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人民服务。”不久文革爆发,做“领导工作”的被打倒在地,做“掏粪工作”的也难逃厄运。当然在中共话语系统中,除“领导工作”与“掏粪工作”外,还有诸如宣传工作、外事工作、管理工作、后勤工作、统战工作、技术工作等等。然而还有一种应用更广泛的工作,这就是“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一词从表面看近似劝导,但在中共恶行却赋予更多内涵。从中共匪首到掏粪工人,人人都可做“思想工作”。考察这“思想工作”始于何时,大概很难讲清。不过有一件逸事,可算是最早的“思想工作”了。
那是在1933年,介公围剿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政府控制的地盘也称中央苏区,这一地盘位于大陆腹地,却要挂上“苏维埃”的牌号,何其荒唐?一个国家应当有两个政党,但不能容忍两个政府同时征税。介公扫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方法,是在中央苏区周边修公路建碉堡并调运粮草,继而对中央苏区政府进行围逼清剿。苏共魔头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为扶植中华苏维埃政府,派奥地利藉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作为特派员入驻中央苏区,以加强反围剿的力量。读过中共党史的大陆知识分子知道,此人正是李德。
李德实际成了反围剿的中共指挥者之一,苏区政府替他单独建造了房屋。李德可不像中央苏区的那些中共头目那样虚伪,他直率提出要求:希望夜晚有女兵陪睡。解决李德的陪睡工作,若在今天的大陆完全不成问题,但那时却有困难,因为苏区的年轻女子见到李德就吓得躲开。据说这位洋领导高大粗壮且手臂多毛,她们担心自己身体承受不住。彼时近邻有共青团机关,住着一名团组织的头目,其妻有几分姿色。这令李德垂涎三尺,他见缝插针主动送礼,自然意在勾搭。这个共青团的头目感到危机,又不敢指责共产国际派来的领导,只得向中共更高层反映求助。那时中央苏区主要领导是无锡人秦邦宪,即博古。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共打江山的大员,不能像对待普通士兵那样批评教育。博古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替他找个临时太太解决陪睡工作。找怎样的太太呢?中共要员们研究后认为,物件不仅应当年轻,而且要身体强壮、人高马大。因为据说不符合如此标准,就难以满足李德的陪睡需求。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贞奉命在团中央找到一名符合要求的青年女子,名叫萧月华,广东人,原是没文化的童养媳,比李德小10岁。读者诸君请注意,此事绝非我凭空杜撰,原中共大员朱德的夫人康克清,熟知此事全过程。此外,《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7.)与《延安秘史》(梅剑红旗出版社 1996.9.)等文献,对此事都有具体记载。
萧月华和大多数女子一样,对高鼻子篮眼睛、连语言也不通的李德,全无丝毫好感。况且夜间的陪睡工作总不能闷声不响地进行,如果陪睡的床边再安排一个翻译,恐怕不合适吧?
办法当然有,再大困难也难不倒中共,这个办法就是本文要谈的“思想工作”——由中共组织出面做萧月华的“思想工作”。李坚贞代表组织是这样对萧月华做“思想工作”的: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临时当老婆也是工作——陪睡工作,而陪睡工作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思想工作”结束前,还加了一句:“组织上已经决定”。总之,对萧月华的“思想工作”做得很顺利,在萧月华的脑子里,很快形成一种观念,即李德同志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又是对陪睡工作有需求的领导。夜晚到李德同志身旁从事陪睡工作,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既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于是,被做了“思想工作”的萧月华,同时也是根据“组织决定”,抱着“为革命事业决定献身”的态度,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陪睡工作。
“思想工作”一抓就灵,甚至不久到延安萧月华还产下男婴,张闻天、朱德都来祝贺,毛泽东还派贺子珍送来礼物,但萧月华和李德的关系却形同陌路。这也难怪,鸡与鸭无法沟通,“思想工作”的力量不是无限的。萧月华作为童养媳出身的穷人,虽不懂每个人应享有自由的权利,但每夜都要违心地献身陪睡,那滋味恐怕没那么舒服。幸好到延安后,萧月华被安排到抗大学习,周六才回家。李德的陪睡工作无法保证,于是重新寻找陪睡者,继而看中歌唱演员李丽莲。李丽莲于1937年5月与蓝蘋一起投奔延安,蓝蘋即后来在文革中令人闻风丧胆的旗手江青,在与演员金山同居被抛弃后,转而投奔延安并更名江青。事实上延安时期从事陪睡工作的女子,远不止萧月华、李丽莲等人。“陪睡”已蔚然成风、毫不足怪,公开的陪睡者们还获得“临时夫人”这一浑号。如当时日共领导人野阪参三,及另两名苏共驻延安联络员,都各有一名“临时夫人”,事先还声明回国时不带走。曾经也属中共重要头目、后于1953年又成了反党集团头目的高岗,当年从延安到东北的战火生涯中,瞒着自己老婆n次追寻“临时夫人”陪睡,其成功率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当然,高岗暗中捕获“陪睡者”,靠的也是“思想工作”这一妙招,不过此时的“思想工作”不用别人代劳,全靠当事人高岗自身一张嘴。顺便带一句,李德到延安后看中的“临时夫人”,倘若不是李丽莲而是江青,文革史上的“四人帮”也就少了一主角。
“思想工作”很神奇,通过做“思想工作”,既可成功促使一个女子献身陪睡,也能将一个女人从丈夫的身边拉开。曾经官至国防部长的彭德怀,1938年在延安趁机虏获知识女性浦安修,并结为秦晋之好。此后在21年的岁月里,夫妇间感情笃厚。但到了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因彭德怀的那个“万言书”中,对大跃进稍有微词,被毛泽东定性为“向党进攻”。彭由此遭尖锐批判,并遭革职罢官,从此厄运缠身,直至文革中惨死。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原本只做别人“思想工作”,庐山会议后,开始变为别人做她的“思想工作”,甚至每次到京郊的挂甲屯看望彭德怀后,组织都要找她做“思想工作”。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所做的“思想工作”,其中首先要求她与彭“划清阶级界限”,其次还必须汇报彭的思想动向。浦安修遭遇的“思想工作”,与萧月华遇到的“思想工作”又不同,不仅是压力大小不同。“划清阶级界限”主要是指与彭德怀离婚。
八届十中全会后,北师大党委做浦安修的“思想工作”,已是明确强调必须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不愿离婚,但浦安修在压力巨大的“思想工作”面前,深感走投无路。经历了无数次痛苦的挣扎,她终于向学校党委递交了一份离婚申请。我估计刘少奇的一句话,使浦安修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也是促成浦安修决定离婚的重要因素。刘少奇讲过:“别人可以平反,唯彭德怀永远不能平反”。浦安修的离婚申请又被上呈至中南海,最终不置可否。不过浦安修离婚的决心却日益坚定,离婚至少可以减少令人头皮发麻的“思想工作”。
分手的日子终于到来,彭德怀拿着一只梨动情地说:“安修,如果你相信我彭德怀是无辜的,你就别吃这半只梨(象征分离);否则……你就将你那一半吃掉……”沉默有倾,浦安修终于拿起那半只梨义无反顾地吃了,剩下另半只被彭德怀狠狠摔在地上,从此21年的夫妻之情瞬间一刀两断,“思想工作”的威力尽显。
“思想工作”可以使萧月华们顺从地陪睡,也可以令彭德怀的夫妻关系嘎然中断,这大概是中共“思想工作”的威力。然而不要以为“思想工作”只有在男女离合的问题上才有作为,要知道“思想工作”的空间无限宽广,就连体育竞赛中,谁将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也能依靠“思想工作”决定。
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前4名,全是大陆选手——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和张燮林。四雄争冠,谁将成为本届男单冠军,按理应看这4人的实力、心理素质与临场发挥了,观众享有欣赏乒乓球真实的顶级鏖战的权利。但赛前一天,堂堂元帅兼副总理贺龙,秘密召开了主题为“谁来当冠军”的会议,会上这位元帅不容置疑地放出一句话:“我们让谁当,就是谁当了”。最后依然是这位副总理一锤定音:“让庄则栋当冠军!”当然,这也是“组织决定”。
让庄则栋当冠军的“组织决定”如何才能落实?方法也是做“思想工作”。于是,贺龙亲自做徐寅生的“思想工作”,教练傅其芳做李富荣的“思想工作”,上海队教练做张燮林的“思想工作”。徐寅生、张燮林深知顺从是最稳妥的策略,拒绝“思想工作”意味着什么后果?他们当然很清楚。总之,对徐、张的“思想工作”一抓就灵。李富荣口头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已受伤害的内心却是五味杂陈。次日决赛,庄则栋终于“力克群雄,勇夺冠军”,而整个世界却被蒙在鼓里。此后在1963年、1965年的第27、28届世乒赛上,李富荣又连续遭遇同样的“思想工作”,因为组织上认为“中国需要有三连冠”,以便让全世界震惊,你李富荣难道这点爱国主义道理都不懂?早期的萧月华为革命陪睡,到此成了李富荣为祖国而“假打”。中共的“思想工作”,终于成功蒙骗了全世界无数球迷,也奠定了大陆打假球的传统。
文革结束后,中共的“思想工作”这一法宝不会丢弃。伴随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也不断出现。2012年安徽定远县站岗乡齐某,伙同另二人以介绍职业为幌子,先后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拐骗妇女达300余人,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拐卖妇女的流水线,似乎具备企业化经营的格局,形成供销配套的规模。
这一切,难道与“思想工作”也有关?当然有关!被拐骗的妇女,有些是转销到穷乡僻壤,一些娶不起妻室的穷汉,成了妇女交易市场的买主。他们取出全部积蓄,凑足定额买下被拐骗妇女为妻。为防备买来的老婆逃逸,买主及其父母的主要方法,除严密监视外,就是对被拐骗妇女加强“思想工作”。另一些被拐骗妇女,则被卖到社会底层的性交易机构。对于其中拒绝提供性服务的妇女怎么办?方法同样是做“思想工作”。
几年前我在银屏前观看一档法制节目,萤幕上是记者采访性交易的经营者,(明清时称老鸨,也是妇女买卖市场上最大的买主)。记者问:“她们(被拐卖妇女)拒绝提性供服务怎么办?”
经营者认真地回答:“我们会做她的‘思想工作’”。
原来“思想工作”还有逼良为娼的功能!听了经营者的一席话,刹那间我似有所悟,原来听起来近似劝导的“思想工作”四字,恐怕其中内涵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得多。由此进而觉悟,半个世记前的文革中,要想使学生揭发老师、使妻子揭发丈夫、使儿女揭发父亲,最常规的方法必定是“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的威力,还在于能激励人们加入广泛的互斗、恶斗乃至往死里斗,这在文革中早已充分显示。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一次演讲中谈起语言的腐败,在我看,语言腐败最严重的一个词,也许正是“思想工作”。
然而,现今许多二奶们对贪官的揭发,大概不必依靠“思想工作”;重庆王立军揭发主子薄熙来,肯定也毋须“思想工作”。在我的话语习惯中,也从未使用过“思想工作”一词。有意思的是,像我这样历来对“思想工作”敬而远之的教书匠,居然也写出通篇全是关于“思相工作”的文字,这一点就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22/n108680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