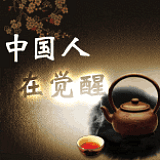在京剧界,“须生”指表演老生的演员。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须生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被称为“四大须生”。其后,高庆奎因为嗓疾而渐退舞台,余叔岩和言菊朋于40年代先后去世,“四大须生”的提法随即有所变化。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他们各具特色的表演,为他们赢得了无数赞誉。
随着中共于1949年建政,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周信芳的命运也随之起伏。其中比较“幸运”的是杨宝森,他于1958年病逝,没有经历文革的惨烈,而其他几位或含冤被迫害致死,或身心受到伤害。
1965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等人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这成为毛发动文革的导火索。曾主演京剧《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牵连,被江青赶出了北京京剧团。文革爆发后不久,马连良被打成“汉奸”、“戏霸”,还被抄了家,古董、文物和有价值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后,他被关押在北京中和剧院休息厅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内,并时常被揪出批斗。
据其弟子回忆,马连良在被隔离期间,一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手执鞭子,闯进所谓“黑屋”,命令里面的所有人都跪下,让他们逐个“交代”每人挣多少钱,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交代”后,“红卫兵”又大声斥责:“你们挣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发给十二元生活费。”还有一次,开会批斗所谓的“走资派”,马连良被强迫陪斗,其衰弱之状让人心痛。
凌辱和恐吓将马连良吓的人体浮肿、不能进食。1966年12月的一天,马连良在买完饭后摔了一跤,16日即含冤去世,时年66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至今不明白,我怎么了?我为什么这样了?不明白!”
此时在上海担任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周信芳的命运也同样令人扼腕。1965年,为了抵制江青,周信芳曾在上海京剧院党总支会议上批评江青让剧团停止演出,单打一地排“样板戏”,耗资人民币几十万,指责这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不久,上海《文汇报》开始连篇累牍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爆发后,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就被扣押在京剧院交待问题。红卫兵则直冲周宅,用砖头石块砸家养的警犬,用军用的皮带抽打其儿媳敏祯,揪住孙女玫玫要给她剪牛鬼头示众。敏祯被打昏,玫玫被吓疯。
据《周信芳传》记载,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他被反剪双臂挂牌示众,“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周夫人裘丽琳则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开肉绽,最终卧床不起。
1968年,张春桥亲自批捕了周信芳。接着,又抄周家,并拘捕了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获释,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夫妻、母子没能见上最后一面。1970年,周少麟因说了江青就是电影演员蓝苹这样一句话,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劳改营。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含冤去世,终年80岁。
而身在石家庄京剧团的奚啸伯在文革时也被扣上了“反动艺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发50元的生活费,后来被降到15元。生活水准的骤降,精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并患上了急性肺炎,后来还因为中风偏瘫。
1976年5月,奚啸伯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弟子欧阳中石说:“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他们(造反派)问我什么,我都承认,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我说的,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所以,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1977年12月10日,奚啸伯悄然去世,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他只给儿子留下了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和未了的心愿。
另一位在北京京剧团担任副团长的谭富英一直心向中共,于1959年成为中共党员。令人颇有微词的是,在文革批判一些同行时他不吝言辞,失去了传统做人的忠恕标准。其后,他被江青等人勒令退党,遭受了一些迫害。1977年,谭富英病故。
一代著名须生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艺术生命。若地下有知,他们该明白到底是谁让他们活得如此不堪的吧。
(看中国:http://kzg.io/gb3i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