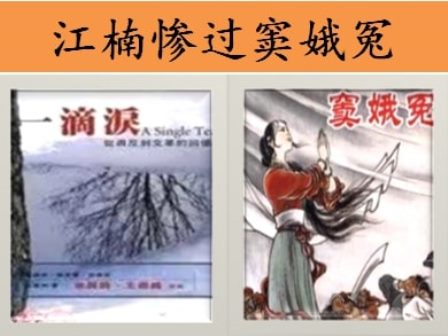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代表作《感天动地窦娥冤》,其中反映的元代官吏草菅人命,老百姓有怨无路诉令人发指。但大陆文革时期真实的江楠案,较此惨烈百倍,且至今仍未完全申雪,必须追究到底。
在巫宁坤教授的传世之作《一滴泪》中,提到安徽大学俄语讲师江楠的惨死。江楠是印尼归国华侨,她为人温和善良,乐于助人。其丈夫林兴(1919-1993)曾出使保加利亚,六十年代初,他们夫妇被排挤出外交部,下放到安徽大学后林任工会主席,文革后得以幸存。曾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讲述称江楠受他牵连,被下放到农村,因为长得漂亮,被安徽大学工宣队的几个人轮番奸污,含冤自杀,尸体埋到荒郊野外,被野狗吃得只剩下白骨。
追根溯源,江楠的惨死,是由于受到纠缠林家三兄妹——林曾同(1917-1969)、林兴、林锦双(傅秀,1921-2001))——多年的所谓“电台案”的株连。而这宗“电台案”起因于抗战时期,身为地下党员的林锦双为掩护“同志”而收藏一只“黑箱子”。
说来话长,且慢慢道来:
话说林氏三姐妹之父林步随是林则徐曾孙,曾任中国留美学生总监督和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抗战爆发后,他已寓居在家,但有民族气节,决不和日本人合作。
1942年5月的一天,地下党直接领导傅秀的张宏飞,提着一个小黑箱子到林家,叮嘱要收藏好,傅将之藏在自己屋里床下。几天后,地下党有叛徒供出林家是抗日据点。傅奉命紧急转移,行前匆匆交待大哥林曾同替她保管好那个黑箱子。
翌日夜间,日本宪兵队跳墙进入林家抓人,扑了空,留下三人蹲守,把全家人看管起来,连瘫痪在床的林步随也不例外。林家是个三进三出的大宅院,房间很多,日本宪兵队急切之下来不及翻每个箱柜,毫无所得,悻悻而归。林曾同突然想起妹妹的交待,趁看守不备溜进傅秀的屋子,打开箱子一看,发现里面全是电讯器材(电子真空管)。他和弟弟林兴在看守的眼皮子下一个放哨,一个动手把电讯器材分散,藏在壁炉烟道和屋内顶棚里。傅秀离开北平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前,曾悄悄回家拿御寒衣服,才得知箱子里装的是电讯器材。
日本宪兵队一直盯着林家,半年后,他们又把林兴抓走,对他动刑,逼问傅秀的下落。日本人先是用毛巾蒙着脸浇凉水,但林兴喜好运动,能憋气,日本人又灌辣椒水,踩肚子,坐老虎凳,严刑逼供,但他确实不知妹妹的下落,日本宪兵队抓不到把柄,最后只好放人。
中共建政后肃反运动中,林曾同在自传中主动交代了掩护这箱电讯器材的事,结果惹出麻烦。他所在单位把这当做大事,派人外出调查,幸好找到当事人张宏飞,证实那是他存放的抗日捐赠物资。调查人员又专门去了林家,果真在壁炉烟道和屋顶棚找到存放的电讯器材,其型号和年代,确是当年的产品。经过一番审查,最后给此事做出“存放的是抗日电讯器材”的正式结论,并把结论抄送给傅秀以及林兴夫妇所在的单位。
文革浩劫中,除供职于安全部的大哥1969年病逝外,剩余两兄妹先后大祸临头,他们年轻时为抗日救国而投身的这场革命变了味。
傅秀首当其冲,她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很不理解,在家里和别人议论说肃反时康生如何在北京医院装病,躲避审查,而医生们认为他根本没有病;还说了江青在北京医院养病时如何整治护士,如让护士一天给她织一件毛衣,还强迫护士跪着给她洗脚等。傅秀担心这帮人上了台,国家可要遭殃了。
结果祸从口出,她的朋友将她出卖,将此材料汇报康生。康生亲笔在上面批示,说她是“杨献珍的走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5月,她从家里被抓走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关到秦城之后审讯者对“炮打”一事绝口不提,只是再三追问燕京大学地下党和电台问题。
原来他们推翻了以前的结论,硬要把电讯器材零件说成是电台,把为抗日捐赠说成是为联络敌伪,他们上挂以刘仁为首的北平地下党,下连燕京大学的抗日知识分子们,甚至把外籍的夏仁德教授为燕大学生收藏过抗日文件也说成是燕大地下党被外国人操纵。燕大女同学何美一(后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因为去林家被日本人带到警察署审问过,文革中也被关进牛棚。
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首先指向了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北平地下党已被文革权贵们定为特务党,但一直也没有抓住任何证据说明它有问题,直到1968年夏天彭、刘专案也无法定案。此时,毛泽东和文革权贵们急着召开九大显示“胜利”,因此提出“专案工作要为政治服务”,给了专案组“先抓人,后找证据”的权力,首当其冲的是燕大地下党,他们以“电台”事件开刀,重翻旧案。
从1968年夏到1969年秋,林家兄妹接连遭难,先是傅秀被关进秦城监狱,然后是林兴被宣布有严重问题,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牛棚,江楠因此被下放农村,被工宣队轮奸,自杀身死。这一连串残害林家人的事件谁是主谋?
1968年6月,江楠长子高文宜打听到地质部军代表郭毅住在报子胡同(傅秀在地质部工作),便硬着头皮闯到他家,郭毅是个老军人,一见面他就劝高不要再写上告信了,他说:“批准逮捕你母亲的就是总理周恩来,他是根据辽宁大学造反群众的揭发,并没有向地质部核实,已经把此案交给中央一专办彭、刘组(中共中央第一专案审查办公室彭真、刘仁组)管,只有地质部专案组的人才能和他们联系,我们都不能过问。”高很震惊,原来是周恩来批准抓她母亲的,周是中央一专办牵头人,出面替康生报私仇。他明明知道傅秀在自己家里议论康生并没犯法,但还是强行逮捕,先抓了人,后找证据。把江楠关进秦城之后,他们捏造了一个假罪名:将当年为抗日出力的林家说成是敌伪特务的联络点,把被掩护的电讯器材零件说成是敌伪电台。他们在地质部成立了江楠的专案组,在安徽大学成立了林兴的专案组,专案人员受一专办彭、刘组直接领导,而一专办向总牵头人周恩来汇报。
四人帮倒台后高见到二舅林兴,证实了中央一专办彭、刘组就是他被监禁审查的幕后指挥者,林兴说:1968年11月,工宣队接到一专办的通知后,立即成立了林兴专案组,把我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的牛棚,把江楠下放农村。他们反复追问我,1942年夏掩护电讯器材的经过,以及当年你母亲带我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经过。很显然他们想要从我口里找出疑点去整你母亲。当年日本宪兵队想从我口里得到你母亲的消息,他们拷打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是什么也没得到。这次是工宣队,他们逼我交代你母亲的问题,揪斗游街单独监禁,仍然什么也没得到。可是工宣队祸害了江楠,只剩下从荒野里捡回来的骨头,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说着说着泪水顺着这个硬汉子的脸膛哗哗流下,这情景深深印在高的脑海中。
当年的“中央一专办”权力之大可与当今的“中纪委”有一比。高曾亲身同一专办彭、刘组的军代表们打过两次交道,他们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宽街一所幽静的院落内。
第一次打交道是在 1968 年秋,高以给母亲送几件冬衣为由,问他们傅秀究竟有什么问题,他们神情紧张,避而不答。反过来追问高是谁告诉他一专办地址的,声色俱厉的要高揭发母亲的“罪行”。原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能证实林家罪名的材料,正在气急败坏之时,得到傅秀的同父异母妹妹林子东的揭发材料。
林子东交代说:“电台来路可疑,傅秀是鬼域人物…”“1956年傅秀在全聚德招待为电台案做证明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对抗审查的攻守同盟…”。
专案组如获至宝,逐条逼问。他们得意地说:“林子东都说傅秀是鬼域人物,她绝对不会诬陷自己姐姐的。”于是总参海运仓学习班开大会批斗高的父亲,专案组对之辱骂恐吓,动手打人,不让睡觉,不让回家,非要高父亲承认傅丽是特务。连陪斗的张先生也不能忍受这种人身侮辱,跳楼自杀摔断了脊椎骨。
林兴就是在这时被一专办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他与忧心忡忡的江楠分了手。但是一专办从林兴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第二次打交道是在1974年夏,一专办彭、刘组副组长、军代表唐某找高谈话,此时江楠已经惨死,傅秀被关秦城六年精神失常,拒食脱水,奄奄一息。为了救母亲,高曾求外交部龚普生大使将他的求救信转交给邓颖超,据说邓接过信后连一眼也没看便扔在桌上,严肃地批评龚大使说:“以后少管这种闲事,不要给恩来惹麻烦”。
高很不平,明明是周恩来非法抓人,把他母亲监禁到奄奄一息,也不让治病,这是“闲事”吗?这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女人,内心真是冷酷无情,胆小自保,见死不救。
幸运的是高还有另一封信,由他父亲转递叶剑英元帅,据说叶帅批示要一专办治病救人,一专办才不得已找高谈话。这个谈话的人姓唐,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的,他说:你也不要到处写信告状了,信都转到我这里了,我们安排你母亲去复兴医院,“保外就医”总该可以了吧。唐某还恶狠狠地说:你母亲议论康生和江青同志是有罪的,你要划清界限。
中央一专办替权贵们报私仇有恃无恐,对被审查人却“查明无罪,也不释放,关死为止”。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释放任何犯人都需要经过中央一专办的牵头人周恩来签字,而周恩来要等到文革权贵同意才肯签字。高母亲的案子涉及康生、江青,释放她要经他们同意才行,这如同与虎谋皮。实际上,林家的“电台”冤案早已查清, 连捐赠此箱抗日器材的人和直接经手的人都找到了,并且做了证明,一专办还是不结案,林兴仍然不能释放,就这样放走了残害江楠的工宣队,使他们平安回到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犯罪人互相包庇,至今逍遥法外。
文革把一批马鞍山钢铁厂的工人送进安徽大学,让他们有机会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中央一专办指使工宣队关押林兴,使他不能保护妻子。这些举措激发了马钢工人的丑恶的欲望,他们趁火打劫,轮番侮辱强奸了被审查人的妻子江楠。
江楠人长得漂亮,会打扮,穿着洋气,与当时一片灰蓝的众人色调不同。那班工宣队员早就垂涎欲滴。
经过是这样的:
1968 年冬,工宣队故意把林兴、江楠夫妇分在两地,先是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宽严大会上宣布林兴有严重问题,把他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牛棚内,随后又把江楠下放农村。工宣队头目们借调查林兴问题为由,在谈话地点轮奸了江楠,并威胁说如果胆敢泄露,将严办林兴。孤独无助的江楠上告无门忍无可忍,曾将此实情告诉过知心好友李怡楷,她是巫宁坤的夫人。
不久江楠发现自己有孕了,她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去医院打胎。但那时打胎必须提供男方姓名。这个头目不但不给开信,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露工宣队强奸她的秘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江楠走投无路,想到将要带着这种奇耻大辱活一辈子,她痛不欲生,曾对好友吐露过唯有一死了之。江楠还凄惨地说:如果有一天看到她的窗前摆着一盆花,那就是她已经走了,请在林兴获得自由之日,转告他江楠是清白的。
据《一滴泪》记载,江楠是在她所住的社员家上吊死的。这帮毫无人性的马钢工人在伙房墙上门前贴满黄纸标语:“江楠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
《一滴泪》说“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有人不忍心挖了几锹土盖上…”。后来林兴告诉高更多更悲惨的情景:“她的坟再次被盗,盗走了她身上仅有的衣服,留下赤身露体的江楠躺在荒野里多日,野狗把尸体撕咬得残缺不全,只剩下白骨…”社员愤怒地质问:“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
文革后江楠一案虽然得到平反,赔了一点钱,但是对犯罪人的调查至今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
江楠含冤而死,但是《一滴泪》记录了她生前身后的悲惨遭遇,它告诉世人发生在五十年前安徽农村的一幕:工宣队集体残害一个被下放的普通女知识分子,死后她被暴尸荒野,任凭野狗凌辱尸体的真实故事。
高文宜写道:
江楠自杀是受我母亲案子的牵连,冤有头,债有主,写出来为历史作证,为把所有涉案的恶人包括始作俑者中央一专办和它的牵线人都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这些披着人皮的鬼魅再也不能害人了,让江楠在天之灵得到安宁。(《我所知道的江楠之死》,2010年9月9日,写于美国马里兰州。载于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
读者至此可以洞悉,“人民的好总理”及其妻子——外表慈眉善目的“邓大姐”,会丧心病狂地为讨好康生、江青一伙,公然以别一面孔示人。周置自己外交部的老部下于水火,邓训斥前来求助的老同志。笔者曾在《黑白参半周恩来》中披露了周若干劣行,看来实在是挂一漏万。
人生有限,学问无穷。鲁迅斯言值得我们深思。世事洞明皆学问,我们都要努力提高识别能力,即粤语所谓“带眼识人”!勿受其美誉或面具迷惑轻信,谨以此与诸君共勉。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4/17/n137135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