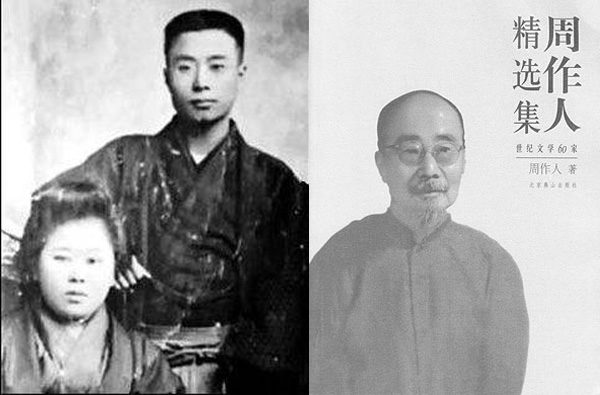一个人今日之结局,也许正是昨日自己抉择的后果。这句话若用于评价周作人先生,大概是贴切的。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住在北平八道湾的周作人受传讯,当年12月被拘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受审,与他接受伪职一样,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法院原判徒刑14年,因胡适及北大校长蒋梦龄等人的斡旋,得以改判为10年。周作人在狱中虽失去行动自由,但未失去言论自由,依然从容笔耕,当然也未吃苦头。之后又因时局变动,实际服刑2年半即释放。
1949年1月,保释出狱后的周作人,因无法返回北平而流落上海,暂栖身在他的学生尤炳圻寓所的亭子间。尤宅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从这里向北,曾经是日租界。老一辈知道,1949年以前这一带颇有“东洋味”。周作人心念著新街口的八道湾,对上海的兴趣似乎不大。话虽如此,在上海短暂的日子里,他还是留下《横浜桥边》一文,只是孤陋寡闻如我辈,未能涉猎而已。同在这段时间内,胡适也在上海。这是因北平沦陷在即,介公“抢运学人”的计划在实施中。胡适与周作人惺惺相惜,深知周作人在中国文化方面功底深厚,兼又熟悉古希腊与日本传统文化,数次电话邀见周,意在挽周同赴台湾。何去何从?周作人面临一次重大抉择。周作人若到台湾谋一教授席,以他在文坛的声望,当然不成问题。可惜胡适的热心,每次都为周婉拒。
尤其是古道心肠的俞平伯。1946年周作人陷刑事审判时,俞平伯即力促胡适设法帮助周作人。在上海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俞平伯依旧想成全周作人,催促胡适联系周作人。当发现周作人完全没有赴台的意愿时,俞平伯无奈地对胡适说:“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那些与旧政权关系很深的朋友,比如你适之,他可能不想有更多牵扯”。胡适眼看无望,只能带着遗憾离开大陆。从此,这两位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永久断裂了关系。
二
俞平伯说“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此一说恐非空穴来风,但很少有人注意。周作人与俞平伯既有师生之谊,又有朋友之情。俞的散文集《燕知草》有周作人题写的跋,其中有周对明代公安派文风的精彩评价。1936年林语堂赴美前夕,朋友相聚饯行,画家汪子美以此为题画成漫画《新八仙过海图》。画中俞平伯成了蓝采和,靠得最近的周作人成了张果老,林语堂则是吕洞宾,当然还有其他朋友也成了画中仙。周、俞之关系由此可见,俞评周对新政权“抱有希望”,当然不是信口开河。
事实上,周作人与中共“新政权”的交往,可推溯至上世记20年代初。早年在日本留学开始,周作人与著名小说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有深度交往,遂接受新村主义思潮。回国后又在《新青年》上撰文专谈新村主义。新村主义作为乌托邦的一种,源于法国,系无政府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杂合物。巧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当初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读过《新青年》上周作人的文章,也曾将新村主义奉为圭臬。1920年4月7日,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的毛泽东,专程拜访周作人。当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毛泽东君来访”几个字。周作人与中共早期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也是私交甚厚。李大钊被捕后受绞刑而殁,周作人曾寄予深切同情。此后李之遗稿是他保存,李之子葆华亦获他掩护约一个月。李大钊生前极力传播共产主义,向知识界解绍苏俄“十月革命”,宣扬苏俄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客观而言,斯大林是上世记与希特勒、毛泽东并列的极权主义三大魔头,共产主义完全是人类最恶毒、最阴暗的邪教。李大钊的行为无疑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对苏共灭绝人性的滔天罪恶作掩饰。对此,历史早有公论,毋须赘言。
周作人在出任伪职期间,与中共地下党依然有联系。周帮助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赴延安,临别时嘱咐:“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对他带好”。李之另一女炎华,也曾获周作人经济上的帮助。炎华的丈夫侯辅庭,靠了周作人才在沦陷后的北大临时当职员。侯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周在事先同样是清楚的。“五·四”以来,周作人在文坛光彩夺目,其后人们为他在日寇侵华时期出任伪职而扼腕叹息,而他与中共的关系,在大陆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中缘故不难琢磨。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使周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
1949年7月4日,出狱后的周作人,给“新政权”写了一封约6000字的信,信是写给周恩来的。信末写着:
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毛泽东当然看过此信。次年,周恩来将信交文化界的郑振铎、沈雁冰等人,作家唐弢也看过信的原件。据唐弢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谈到,信的内容分两部分,一是表明自己对“人民政府”(新政权)的看法,二是为自己辨解,希望能回八道湾寓所(其时北平大概已改称北京)。“用旧时新闻记者的笔法,前者叫‘拍马屁’,后者叫‘丑表功’”(见唐弢《关于周作人》,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5月号)。不久,周作人获许他回八道湾的指示。他欣喜地告诉朋友:“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允许我回家”。那口气里流露出的,竟是诚惶诚恐的低声下气。
三
周作人写给“新政权”的那封信,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资料。这封信今在何处,似乎没人提过。看过原信的人早已作古,当然也不可能作认真分析。唯有体制内作家唐弢,文字婉言传达了周作人催眉折腰的“拍马屁”。这使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画家陈丹青的书上,有一帧照片,与此恰成鲜明对比。照片上正是日寇投降后,周作人行走在被警局传讯的路上。那画面上,个子不高的周作人,一袭淡色长衫,意态翛然、神情自若的名士风貌,哪里像是被警局传讯?近靠他身旁的,是拘押他的民国警察。看那警察头戴大盖帽穿着短裤,倒像是周作人的随从或听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名人的所谓气场吧!
回到八道湾的周作人,似乎想对“新政权”表示自己臣服的忠心。1952年,他一反当初带有反抗色彩的文字风格,写出《伟大的祖国》一文,文中说:
在这样伟大的祖国里面,能够当一个人民,这也是够光荣的事了,现在我们的义务是要怎么的来报酬这光荣,至少也要自己保重不辱没了这光荣才好。(原载《亦报随笔》1952年1月7日)
“新政权”的累累罪恶,早已罄竹难书,此处毋须赘言。周作人对“伟大的祖国”或“新政权”的讴歌,与在北平因汉奸罪被传讯时相对照,反差实在太大,简直判若两人。可惜1949年后,急于歌功颂德的文化人批量涌现,哪里轮得上你周作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周作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对于这一致命的判决,周作人难道也茫然无知?周作人也许不清楚的是,1949年他给“新政权”写的那封信,已是稳坐江山的毛泽东,看后撂下一句话:“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其中“养起来”三字颇值得玩味。一猫一狗一宠物皆可“养起来”,对老人也可“养起来”,周作人究竟归哪一种“养起来”?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回忆起50年代前期,弟兄二人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相遇。简单的寒喧之后,周建人已意识到:“……知道他(周作人)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1期)。
周作人对“伟大的祖国”的歌颂,声音显得太微弱,几乎没人在意。终于他也就死了心,退而当一名“隐士”。周作人在暮年的贡献,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翻译了不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一部古希腊《卢奇安对话集》与一部《伊索寓言》,其译笔自然无可挑剔。1955至1959年,出版社按月向他预支稿酬200元,1960至1965年每月增至400元。这段时间内,先是张东荪大祸突降,接着是“胡风集团”遭全国性围剿,然后是俞平伯、胡适被公开批判,之后又是翻天覆地的整风反右斗争。这一切,周作人虽无法公开发声,但私下不该没有自已的价值评判。然而他选择了装聋作哑,一概充耳不闻、视若无睹。鲁迅曾在《隐士》一文中称:“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周作人正是这样的“隐士”。
殊不知,苟且在“新政权”之下的“隐士”周作人,无论怎样装聋作哑,也是躲得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革暴发,周作人的稿酬中止。其子周丰一于1957年被划右派,降薪几级。全家八口,仅靠在中学教书的儿媳张菼芳,每月70元的收入维持。政权更换时留下来的文人学者,早已各自西东、自身难保。出版社与他直接联系的,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出版社女编审文洁若。周作人在文革中的凄惨遭遇,我们只能从文洁若的文章里窥知一二。
红卫兵冲击周作人寓所,是1966年8月的某日。年迈的周作人,中午被红卫兵拖到院子里,遭棍子和皮带没头没脸的抽打。在红卫兵的眼里,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与当年的文坛盟主,根本不算人,而是十足的“牛鬼蛇神”。周作人没有被活活打死,一是因红卫兵女头目上午光顾时,勒令周丰一交出手腕上名表。作为“摘帽右派”的周丰一,当即默默奉上。所以这头目发话:“不要打头,要留下活口交待罪行”;二是周丰一中午回家,见老父已被打倒在地,苦求代老父挨打。结果是丰一右腿被打断,当即痛得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孙男孙女全跪在院子里,哭着目睹这场永久铭刻在心中的灾难(参见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原载《读书》1990年第6期、《随笔》1991年第5期)。
从这一天起,周家寓所被红卫兵占据,周作人只许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两腿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卧倒在地。再后来,周作人只能躺在铺板上残喘。饿了时,喝点玉米面糊糊就著臭豆腐充饥。走到这一步,受尽凌辱的周作人,不知是否回想起曾经与共产主义头面人物的交往,是否回想起低声下气给“新政权”写的那封信,是否回想起胡适在离开上海前,曾力邀自己同赴台湾的诚意。捱至次年4月底,这位曾经“对新政权抱有希望”的苦雨斋主人,屡屡对丰一哀告:“我已是生不如死,不想再连累你们大家了……”几天后,丰一从单位回到家,发现老父早已断了气。
四
一直以来,大陆知识界将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伪职,视为他个人历史的污点。当然,为之惋惜者,也不泛其人。惋惜的理由认为,周之出任伪职,乃是事出有因。譬如“因家室所累”,譬如“因1939年元旦遇剌所受惊吓”,譬如“因蒋梦龄校长曾委托周作人等4人留守北大”等等。这似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曾引用过南宫博为周作人辨护的一段文字——没有在搜寻原因上努力,而是直抒胸臆的将心比心:
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见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原载1971年5月9日《中国时报》)
字里行间有一种类似宗教宽容的情怀,联想起他平实淡泊、不枝不蔓、流水行云的文字风格,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为之扼腕叹息,正是人之常情。然而在我看,周作人对共产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的同情,又充当李之遗稿保存者,甚至对“新政权”既抱希望,对“新政权”的作恶却装聋作哑,还有他对“伟大的祖国”的阿谀之词等等,恰恰是周作人一生中最不值得原谅的污渍,又怎么能成为对周作人应当网开一面的理由呢?
梁实秋在文中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他(周作人)也曾写信给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是他对于抗日战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夙对于时局,和他哥哥鲁迅一样,一向抱有不满的态度。(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见《梁实秋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当然,“和日”也罢,“和共”也罢,对周作人而言,一切早已成过眼云烟。但后来者应当明白,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周作人晚年的巨大灾难,恰恰是此前他对“新政权”主动抉择的结果。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4/08/a1025518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