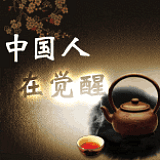“妈,你去美国吧。”郭馨穗望着刚刚被释放回来的母亲,按捺不住心中的悲苦。十多年来,母女俩没有过上一天的安宁日子,被抓、被打、被关押,长期流离失所,身心受尽煎熬。馨穗感到忧虑,她担心长此下去,终有一天她会失去母亲,再也见不到母亲。
在馨穗的记忆中,母亲全身都是病,早早就被医院判了“死刑”。“医生完全放弃了对妈妈的医治,最后甚至连止痛药都不给开了,那时妈妈因病痛,常年都弯腰驼背。”
1995年的一天,郭父用摩托车驮着郭母到公园散心,看到一群人在炼功,横幅上写着“法轮佛法”。“佛法”两个字深深地触动了郭母,她开始跟着学。“一个多月以后,我妈的肝炎、肾盂肾炎、严重的类风湿,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还有很多的其它病,全好了。” 馨穗看到母亲弯成几乎90度的背也直了。
那时馨穗只有十四五岁,就开始跟着母亲学炼。
“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1999年7月,一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中国大陆铺天盖地展开。馨穗在父母呵护下的那种舒适平静的生活在一夕之间出现逆转,懵懵懂懂中,她已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7月20日以后,我们家就开始受到各种压力,光抄家,我能记得起来的就四次。妈妈被送去洗脑班就记不清多少次了。” 馨穗只觉得妈妈回家没几天就又被关押,而警察隔三岔五就来家里骚扰、威胁,家门已被警察踹坏了好几次,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被抢走了。她的世界里只有妈妈、警察、牢狱,除了恐惧,还是恐惧,其它的什么也装不下了。
父亲失踪了
2001年的一天,没炼法轮功的郭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馨穗只记得那天她去给关在洗脑班的母亲送饭,回家后就找不到父亲的踪影。“在妈妈遭受迫害后,我爸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那时已经吓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回家以后我爸就不见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了,也没有留下只字片语,我不知道他是被警察抓了呢,还是离家出走了。什么也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2002年,郭母在被劳教了一年后,终于回到家,直到那时,她才知道孩子的父亲不见了,馨穗一直没敢把消息告诉狱中的母亲,她不想让母亲担心。
母亲回来了,馨穗心里稍感觉踏实些。然而,她没想到,等待母亲的却是一场大抓捕,迫使母亲不得不抛下子女,远走他乡。
母亲被迫远走他乡
“妈妈有一天去市委大院找一位同修,问路的时候竟然问到了当时的市长李大伦,” 馨穗回忆说,“那时市委大院里的人都知道谁炼法轮功,那人一听我妈要找法轮功学员,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市长李大伦。他就开始诋毁法轮功,妈妈就给他讲真相。”李大伦没想到郭母敢和他理论,气急败坏之下,掏出电话就招呼人来抓郭母,但郭母逃脱了。
李大伦亲自下令,督促片区警察围堵郭母。郭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神奇地从后墙仅有人头大小的洞口飞身而出,再次逃脱了抓捕。馨穗至今无法想像,约130斤重的母亲是如何从那个小洞出去的,“那个洞要侧着头才能把头伸出去”。而郭母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只感觉两脚在垫脚的磗上一蹭,瞬间她已莫名其妙地到了墙外。
郭母一时间成了全市通缉的要犯。“为了抓到我妈,他们就把我和我弟送到区政府,分开关在那里。要我们说出我妈的下落。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妈妈去了哪里,也从来不敢和她联系。”
从早上关到凌晨,姐弟俩没给吃一口饭、喝一口水。
“最后实在问不出来什么,就说要把我们送到看守所。管我们那里的两个干警,因为了解我们的情况,人还不错,就拚命保我们,说他们还小,送到看守所也没有用,最后把我和我弟又送回家了。”
回家后馨穗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了自由,没有隐私。“那个时候他们给我派了一个女警,睡觉时跟我一块睡,吃饭跟我一块吃,上厕所也跟着我,就住在我家。”
警方觉得这样贴身跟着馨穗,郭母肯定不会出现,于是撤掉了馨穗的贴身女警。但馨穗不知道此后警察一直在暗暗地跟踪她。
一次突发的事件,让馨穗感到警方为了抓到母亲,甚至使用了更不堪的手段。
刀口下逃生
2003年的2、3月份,馨穗随同修阿姨一起到阿姨的女儿家。因天气冷,两人为了走近道,穿过了一段因拓宽道路而封路的工地。当时,整个工地静静的,没人施工。
“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来四个人,手持砍刀,一言不发,冲着我一阵乱砍,” 馨穗回忆说,“当时我整个人被砍傻了,我完全聼不到任何声音,甚至连疼痛的感觉也没有。”
同修阿姨惊叫,“她还是个小女孩,你们干嘛就……”眼看馨穗一动不动站在那里,阿姨扑倒在馨穗的背上,用自己的身体替她去挡刀。馨穗身上的几层衣服被砍成一条一条的,背上留下了一个一个的刀印;阿姨身上四件厚厚的衣服也被砍穿,背部左侧被砍伤。冬天,厚厚的衣服救了两人。
等馨穗回过神来,凶犯已经逃了。馨穗下意识地抬起双手,左边手腕処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右手背整块肉没了,露出白白的筋骨。馨穗吓得大哭,“阿姨,我的手整块肉没有了……”,就在这当下,鲜血顺着伤口突然急喷而出,染红了手臂和衣服。
同修阿姨把馨穗带到女儿家,家里有人是学护理的,立即带馨穗去了一个小诊所。诊所的医生一看到馨穗的情况,也吓傻了,“天哪,这个地方再砍进去一点点,就砍到动脉,你人就没了。”
“我们不敢去医院,医院看到这个情况可能会报警。” 馨穗说。为了避开警察的监控,馨穗长期躲在阿姨家。其实,警察对馨穗的行踪了如指掌。
馨穗知道母亲有时会和同修阿姨联系,她要阿姨别告诉母亲所发生的事情。然而远方的郭母已有不祥的预感,感到女儿出了事。几天以后,郭母在电话中对同修说,“你说吧,我挺得住。”
流离失所
郭母最终还是放心不下女儿的安全,“我妈告诉阿姨说,你买哪一天、哪一趟火车的票。到了上车的那天晚上阿姨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当时我手上的伤口还包着纱布,艰难地拖着行李。就这样我去了广州,和我妈一起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在那里我们住了十年,期间我妈一直被通缉。”
馨穗前脚走,警察随后半夜2点左右闯进阿姨家。
“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警察当夜跑到阿姨家,用力地砸阿姨家的门。” 馨穗回忆说,“阿姨说,当她开门后,闯进好几个便衣警察,恶狠狠地问阿姨我去了哪里。阿姨说,一个女孩子,这么大的人,她要走,她要去哪,我管得着吗?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已经跟踪了她几个月了,我看到她上了出租车,跟到火车站,就找不到人了。”
“这事是你们干的”
2008年奥运会的前夕,全国各地维稳,弱势群体、异议人士首当其冲,成了严加看管的对象。
馨穗老家的同修阿姨又被警察找上了门。“阿姨就给他们讲大法为什么是好的,也讲到我当时被砍的事情,并拿出砍破的衣服给警察看。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察说,这事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你那被砍的衣服还留着啊?”
阿姨当时就警觉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年,我并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多年的事情,这事就是你们干的,是不是?”阿姨后来告诉馨穗说,“那警察惊慌得脸都白了,马上就从家里往外跑掉了。”
“没有这个人”
2010年10月的一天,广州的气候还温暖如夏,早上8点鈡馨穗出门去上班,刚下楼,迎面碰上天河区小新塘的几名警察。“你是郭馨穗吗?你妈在家吗?”一名警察问到,手上拿着警牌在馨穗眼前晃了一下。“是啊。”几人不由分说拽着馨穗回到了楼上,逼她打开家门。 “再不开门我就砸门了”,警察叫道,门被踹得砰砰响。
郭母从里面开了门,几名警察蜂拥而进,馨穗和母亲被按在凳子上不让动。“他们然后到处翻,抄走了我们的手机、法轮功书籍和资料。”
两人随后被押送到小新塘的派出所。郭母为保护女儿,便对警察说资料都是自己弄的,承担了一切。
馨穗当天中午被释放了出来。几小时以后,大约下午四点鈡左右,馨穗又来到小新塘派出所,她要知道母亲的消息。“他们不承认,说没抓过这个人。我说我上午和我妈一起被抓到这里来的,怎么就没这个人。你再问他,他就不理你了。”
“妈妈音讯全无,我都快急疯了。” 接下来几天,馨穗每日都去派出所询问,但每次的答复都是一样,“没有这个人。”
母亲失去了音讯,这样的日子似曾相似。之前母亲被抓进洗脑班,馨穗天天去送饭,突然有一天,人去楼空,洗脑班和母亲都不见了,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过了好几个月,她被通知到劳教所交生活费,才知道母亲被関进了劳教所,没有经过任何审讯。
郭母被关入湖南的一座大山里
一天睡梦中,馨穗被一阵铃声惊醒,是母亲的电话。这时她才知道母亲被抓到小新塘派出所的当天就被送到湖南的一座大山里被关了起来,山里方圆几百里人车不通,即使逃出看管,在山里也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为了防止郭母象当初一样出逃。
郭母一直和看管的人讲法轮功真相,讲自己炼功后身体奇迹康复的经历。一天半夜里,一个好心的看守悄悄把郭母叫了起来,“阿姨,你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告诉家人这是哪里。”
2011年,郭母从湖南的大山中被释放出来,又回到了广州。那个时候,大陆的监控越来越严,特别是“二代身份证”的实行,个人的所有资料都被记录在身份证上那个小小的芯片中。要抓一个人,非常容易。
出走中国
“在广州,我们躲了十年也没躲过”,馨穗不想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在中国,你哪天失踪了都不知道;哪天这个人就被抓走了,关哪了,也不知道。”
她想,要是能出国,还是离开这里吧。母女俩默默地做出决定,等待机缘。
2014年,郭母顺利地来到美国,其后,馨穗也顺利地出来了。
在大陆那段身心煎熬、东躲西藏的日子,在馨穗的记忆中仍然挥之不去,刻骨铭心。如今,在自由社会里,走在街上,馨穗看到警察,仍不自觉地感到胆怯;听到警车的声音,仍不自觉地感到心悸。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也进入第25个年头。而馨穗及母亲的遭遇只是亿万受中共迫害的家庭的一个缩影。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7/14/n113843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