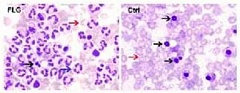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江泽民死讯公开。根据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一旦罪犯、被告人死亡之后就不能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当年纽伦堡审判中不能审判希特勒,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在江泽民死讯公开之际,虽然有很多人感到大快人心、普天同庆,但也有不少人感到遗憾,觉得“就这么便宜它了?”“还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就这样死了?”
其实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法律体系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我对传统文化也不太了解,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一点知识,对江泽民这样的大罪人,即使在审判之前已经死亡的,在他死亡之后也要审查清楚他所犯的罪行,然后根据事实予以判决;即使判决中不一定能够再施以人间的刑罚,但也需要给其定罪,而且由于罪恶太重、所以需要追夺曾经授予他的有关爵位与荣耀。中国现代社会虽然没有爵位制度,但江泽民作为曾经的国家主席所享受的各种待遇其实是与爵位类似的,都需要基于他生前的严重犯罪而予以追夺。
经历了这样的判决之后,江泽民就从一个“一死了之、所以谁也不能再把它怎么样了的前任国家主席”,依据法律程序而成为一个“世所公认、恶贯满盈、虽然逃脱了人间所应当给予的刑罚处罚、但是也逃脱不了人间所给予他的罪恶评价以及追夺荣誉的大罪人”。这对于完善中国国家法制、对于挽救中华民众、对于正确处置和解救那些被江泽民所欺骗、胁迫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办案人员,都具有深远、而且实际的意义。
一、 对于完善中华法制的意义
中国当前的法制体系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现代西方法律体系运用相互混合的一种怪胎、特殊产物。但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还是在最近三百年的现代法律体系中,对于法律本身的定义、对于法律中“人”的定义都有一些偏颇,导致了一些漏洞。
(一) 弥补完善对法律本身定义的缺陷
就法律而言,在古代中国或者在古代西方许多国家,法都是“永恒公平正义”的体现。这种“永恒公平正义”的来源,在古希腊来源于宙斯,在古巴比伦来源于太阳神,在《圣经》等文化体系的国家里来源于神的启示。
在古代中国,法律来源于上天和“道”;例如,来源于汉代董仲舒总结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由此,“道”的精神实质就是法律的真正内涵。按照这种理解,虽然国家政权可能有轮替、会从一批人手中转移到另一批人手中,但是不同政权的法律之间还是有内在一致性的。再进一步说,不同时代的基本是非标准本身是比较稳定、不能变化的。例如,商纣王的许多暴虐行为按照商周两个时代的法律、是非标准衡量是犯罪,经过千百年之后用其他时代的法律衡量也应该仍然是犯罪。这就是中国人对法律的信仰。由于法律本身的最终根源是来源于神、基本的公平正义、天、道……等,而且法律本身是前后各时代内在一致的,所以后代人在运用法律评价前代人、已经去世的某个人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有什么不恰当、不应该的。
现代法律思想对法律的观念就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从程序上,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从思想本质上剥离了法律与神、天、永恒公正之间的关系。法律日益被视为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条文规定,所以,这些法律的表决、签署程序日益成为法律的根源。按照这种观念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认为——法律与永恒的正义没有实质的关系,那么,以此为根源的这种法律当然就存在“不能溯及既往”的问题。表现在审判江泽民上就是,由于中国在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的那个时间之前(江泽民在二零零三年卸任国家主席),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反人类罪”、“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罪”等,日后也就不可能用类似罪名判决江泽民。
但是在现代法律的实践中,对法律定义、罪名溯及力的以上认识也是不绝对的。例如在纽伦堡审判中用“反人类罪”判决纳粹战犯,当时就没有受溯及力的影响(可惜由于另外的认识缺陷,当年没有能够直接审判宣告希特勒本人)。纽伦堡审判所提出的“恶法非法”法理依据,就是认为法律的本质必须与人类的基本伦理、普世价值相互一致,就已经认为“陪审团(法庭)所使用的法律是永恒正义的体现”,而并非只能是“德国、或者某些国家既有立法条款内容的体现”。
总而言之,在古代的中国和西方,法律的根源来自于神、天、道……而不同的皇帝发布、不同的官吏执行的具体的法只是法的不同展现,虽然不同时代、不同政权各自有所不同的表现,但是其根本不变。所以就可以运用这个“根本”来审判过去时代的人。所以,周武王发布、宣告商纣王的罪状就是完全正常的。这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可是在现代西方法律观念体系中,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念体系中,法律的根源是人、某立法机关、某个集团等,所以它就越来越远离永恒的正义,同时也就导致“溯及力”的绝对化、使其不可以用来审判过去的人。这个缺陷需要弥补。
(二)弥补完善法律对人定义、对待方式的缺陷
就如何定义人、对待人而言,古代的法律观念与当代也有不同。由此导致古代法律对人的评价完全可以延续到人去世之后,而且成为后代执政者的责任。
尤其在中国传统的法律当中,注重对于人声誉的评价,而且特别重视对于某人去世之后做出综合的名声评价。对于评价结果不同的人,经常要采取不同的礼节等级予以对待;往往会导致葬礼的不同。而且,如果事后发现被隐瞒的严重犯罪时,还有可能对原来给予的荣誉、封号等等予以追夺。这就把法律体系的作用对象延伸到人的去世之后。
现代法律观念对待人的方式,是完全基于“人的权利”这一个角度来看待。无论是宪法方面,还是在民法方面,各种逻辑都是以“人的权利”作为起点。由此导致,在法律逻辑中,人的权利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法律只能在这个有限的时间空间当中施展其法律的作用。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允许做出很有限的扩展;但是,这种扩展也只能属于该人名誉权(在死亡之后)的延伸,只能被该人的后代继承人发起。如果该人的后代继承人不要求国家机关启动保护,那么国家法律体系是不能擅自启动评价的。
但是,人生在世对社会国家、其他人的影响往往是超越其死亡之后的。例如,孔子的伟大对于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礼义之邦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促进作用,所以在后来的不同朝代都予以表彰,这并不仅仅属于孔子自身的权利,而是国家治理、社会教育本身的需要。那么对商纣王等人的负面评价也是一样。如果按照传统法律体系,在某人去世之后继续依据法律程序而对他进行是非荣辱的评价完全是可行的;甚至有时候是完全必要的,因此也就成为后代执政者、王朝和天子的责任。
就江泽民而言,江泽民对中国国家和人民极端不负责任:他敢于屠杀人民,敢于违反程序出让国土,代表国家签署法律文件;敢于运用贪腐淫乱构建统治官僚体系;敢于当众吐露“闷声发大财”的“当官秘诀”;敢于镇压只是为了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敢于设立“六一零”打碎中国法制,敢于动用国家四分之一乃至更多的财力从而对无辜的民众大开杀戒;敢于出卖国家利益和动用中国外交体系堵住外国媒体和人士的嘴、使其对迫害法轮功不报道、不吱声;敢于绑架和挟持后代中国领导人和执政者对于迫害法轮功不插手……等等行为,其罪恶程度、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都是倾尽整个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如果对这种极端罪恶、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做负面评价,那对于中国的下一步是绝对有害的。
(待续)
文章来自明慧网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1/n139124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