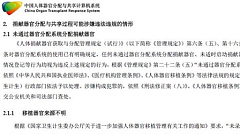一名流亡海外的维吾尔诗人写道,当每天都有数百名我的维吾尔同胞开始消失并被送到“再教育中心”时,很明显我被拘留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我和妻子准备逃离。
塔希尔·哈穆特·伊兹吉尔(Tahir Hamut Izgil)近日在英国《卫报》撰文,回忆了他和妻子如何做出逃离新疆的决定,以及整个逃亡过程的艰难和悲伤,为了保护父母和家人,他无法和他们说再见。以下是伊兹吉尔文章的部分内容。
2017年3月中旬的一天,伊兹吉尔刚刚在乌鲁木齐的新疆艺术学院完成每周一次的电影导演讲座,携妻子一起和新疆喀什来的朋友迪尔伯会面,她讲述了在喀什发生的事情:这几天在喀什地区,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逮捕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市现有的拘留设施——警察局看守所、监狱、拘留中心、劳教所、戒毒所——很快就人满为患。几天之内,许多学校、政府机关甚至医院都被仓促地装备了铁门、窗栏和铁丝网,改造成拘留所和“再教育中心” 。恐惧笼罩着一切,人们说受难的日子就要到来。
迪尔伯表示,这轮逮捕的主要目标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中虔诚的穆斯林人士。此外,曾出国的维吾尔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将被拘留。就在去年春天,在迪尔伯工作的酒店,维吾尔族老板还带领包括迪尔伯在内的约20名优秀员工,到迪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度假旅行。对于多年接待外宾但从未出过国的员工来说,这次度假旅行是非常令人向往和兴奋的。然而现在,这次旅行似乎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迪尔伯前一天才飞抵乌鲁木齐,但随后就接到喀什当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要求她立即返回喀什。 她显然很害怕自己一回去就会被拘留。
此后,伊兹吉尔开始密切关注大规模逮捕的情况。
三天后,当我坐在办公室工作时,伊兹吉尔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他20年前曾与他一起在喀什的劳教所中被“改造”。伊兹吉尔表示,1996年,他本来打算去土耳其留学,但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被捕,罪名是试图将非法机密材料带出境。 其实,他没有什么机密材料,那是任何维吾尔人都可以以任何借口被捕,最终他被捕了。在乌鲁木齐监狱关押一年半后,又被判劳教三年。当获释时,他已经失去了教师工作,没有钱,也没有家。
这名老朋友说,在他居住的喀什东南部的和田地区,曾经一起被关押过的其他几个维吾尔人陆续又被捕了,他感到很快就要轮到他了。
几天过去了。伊兹吉尔给老朋友打电话,但他的手机是关机状态。伊兹吉尔想,再这样下去,很快就轮到自己被送去“再教育中心”了。
2015年,伊兹吉尔第一次看到维吾尔人被以“再教育”为借口强行拘留。尽管乌鲁木齐尚未开始大规模逮捕,但南部地区正在进行的大拘捕行动也开始波及到乌鲁木齐。
近几十年来,无数维吾尔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远郊的家乡搬到了乌鲁木齐,从事各种职业的工作。他们组建了家庭,买了房子,并逐渐将自己视为乌鲁木齐人。现在,他们被远郊家乡的派出所传唤,要他们回家乡,因为他们户籍仍然在那里。在伊兹吉尔居住的小区,每个十字路口的馕饼店都被用木板封起来了,街上的水果摊贩也消失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一片充满生机的街道正在逐渐地变得萧条。
大约在那时,伊兹吉尔的妻子玛哈巴注意到平时很活泼的大女儿阿塞娜从学校回家后心情低落,一回到家就直奔自己的房间,独自安静地待上很长时间。当他们问阿塞娜出了什么事时,她说,在过去的一周里,每天都有一些同学悄悄不见了,被迫与父母一起返回他们户口登记的乡镇,她有几个好朋友也都没来上学。
几个星期过去了,快到五月了,乌鲁木齐的天气逐渐转暖 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伊兹吉尔开车去办公室比平时晚了一点,当我路过八湖梁派出所时,我发现派出所院内出现了异常的骚动。
他透过车窗向院子里望去,大约100名、或许200名维吾尔人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心神不定,身着黑衣的武装特警将他们赶入停在院子里的两辆巴士。一些上了巴士的人在渴望地向院子外张望着。“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 大规模逮捕行动已蔓延至乌鲁木齐了。”伊兹吉尔心想。
一个月后,大逮捕的消息满天飞,在城市的各个地区,每天都有数百名维吾尔人被传唤到数十个警察局并被送往“再教育中心”。 “再教育中心”就是集中营。伊兹吉尔陆续听说许多朋友和熟人都被带走了。
据伊兹吉尔了解,乌鲁木齐和喀什一样,大规模抓捕首先针对的对象是虔诚的信徒、出过国的人以及在国家体制之外自谋生路的人。随后逮捕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其他人群。不过,当局如何确定谁将被拘捕仍然是个谜。被拘捕的人只是被告知“你的名字在他们下发的名单上”,具体什么原因没人知道。维族人都生活在这种可怕而恐怖的不确定性之中。
他在文章中写道,提到被捕人的名单,就要说说警察局里可怕的互联网人员登记系统。从2016年底开始,每个人相关的信息都被输入到一个名为整合联合平台(IJOP)的系统中。有了这些数据,警察——尤其是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对每个他们认为“危险”的人在档案里作了标记。由于每个人身份证信息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一体化平台被查到,当警察在检查站扫描身份证时,档案中有“危险”标记就会触发警报,此人会被当场逮捕。
伊兹吉尔一个朋友的弟弟是电视台技术员。据朋友说,警察是在半夜将他的弟弟从家带走的。没有人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 他是一名优秀技术工人,是团队核心成员。他的亲属恳求电视台高管向警方询问他的情况,但这个请求却被拒绝了,并告诉他们,在目前的紧张情况下,他们无法介入此类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电视台等政府重要机关的工作人员身上,那么没有哪个维吾尔人是真正的安全了。
伊兹吉尔写道,很明显,自己被拘留只是时间问题。他和妻子开始计划逃跑。他们买了去美国的机票——是往返机票,用以消除怀疑——但在四月,在我们试图离开之前,他们夫妇突然被要求交出我们家人的护照。
伊兹吉尔夫妇出国的借口是女儿患有癫痫,需要在美国紧急治疗,恳求女警察把护照留下,但她说收缴护照的命令来自“高层”,她无能为力。
伊兹吉尔写道,“护照”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词。许多维吾尔人只是因为拥有护照而被带送去“再教育中心”。一些维吾尔人非常害怕,甚至主动向警察或居委会上交了护照。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伊兹吉尔和一位朋友分别时,他很想衷心地道别,但不得不压抑住这个愿望。他写道:“当时,由于政府政策上的一个小小的改变给我们带来了拿回护照的希望。如果我们能护照取回来,我们未来的旅行将是一次单程旅行。很明显,如果我们到达美国,就会申请政治庇护,从而成为中共的敌人。经验告诉我,如果警察得知我的任何朋友知道我要出国或对我说了最后的告别,他们就会有麻烦:至少要审讯几周;如果他们不那么幸运,那就会被送去‘再教育中心’,所以我不能让我的朋友因为我的缘故而面临这种危险。如果我要离开的话,我就必须默默地走人。”
伊兹吉尔终于在八月份从市行政办公室拿回护照。三天之内,他们买了机票,卖掉汽车,收拾好行李。他不敢去喀什告别父母。据他母亲说,居委会要在每间公寓的前门都安装一个摄像头,还要求居民支付安装摄像头的费用。
他写道,“这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我没有向父母告别,也没有得到他们的祝福就离开了。这一生,或许就是我的宿命,与最亲近的人没有说再见。”
第二天一大早,伊兹吉尔打电话给岳父岳母,请他们过来,因为他们当天就要去美国,以便治疗女儿阿塞娜的病。岳父母非常清楚阿塞娜没有病,但他们同样清楚政治环境已经变得多么糟糕。
伊兹吉尔写道:“中午时分,我们叫的出租车停在了我们住的大楼前。岳父帮我把行李箱塞进后备箱,我们把背包放在车的后座上。我的岳母从大楼里出来,倒在我妻子玛哈巴身上抽泣着。幸运的是,院子里几乎空无一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含泪告别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借口怕错过航班,催促玛哈巴继续上路。我们敦促老人们立即返回公寓。然后我们钻进出租车,玛哈巴的脸上还挂满了泪水。”
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在机场,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着跑道上的飞机,他转向妻子说,“接受这一切吧,这可能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时刻。”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4/n1404818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