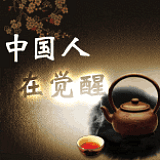上世纪90年代初,借助改革开放的势头,《当代西方经济学》进入大学课堂,马列主义再生产理论渐渐淡出,曾经在这个领域呼风唤雨的如于光远、薛慕桥、刘国光等人,渐成昨日黄花。这里再谈再生产理论的荒谬,当然已无丝毫意义。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A.马歇尔奠基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综合,代表人物是P.A.萨塞谬尔森。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萨谬尔森《经济学》对前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加以赞赏。直至苏联解体,萨谬尔森才在《经济学》中,悄悄把赞赏苏联经济体制的文字抹掉。我不想重复指出凯恩斯学说的谬误,政府干预主义早已不值一驳。我想指出的是,曾被无数人捧为神品天书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这个致命缺陷,就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假设”。人都有自利的一面,如果把这个“经济人假设”抽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便顷刻倒塌,整体新古典经济学大厦也就完全瘫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明白“自利主义”不能概括全部人性的人,又有多少?无数中国学生长期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崇尚集体主义精神,一旦接受经济学的“人的自利主义”仿佛豁然开朗,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人性的真谛。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学生,接受了经济学的“自利主义”假设,走上社会各部门或公司就职,在与方方面面打交道的时候,行为准则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人总是自利的”。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贪图利益、投机取巧,理由就是因为“人总是自利的”。许多人甚至走到“利己而不惜损人”的地步,乃至无数人之间形成心安理得地互害,恐怕都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关。
我不是说“人的自利主义”错在哪里,这样很容易趋向另一个极端——纵容集体主义的欺骗性。“人的自利主义”源自17世纪英国人霍布斯指出的人的“自我保存”的激情,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后来人们由此推导出人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稍后到了荷兰思想家雨果.格老秀斯那里,才完整发现人的自然本性。格老秀斯认为,人的本性首先在于人“必须自我保存”,其次还在于人必须“与他人共存”(即人的社会性)。格老秀斯在德国的后继者普芬道夫认为,“人的自我保存”同“与他人共存”之间存在冲突,能够化解这种冲突的,只有基督教。另一位颇受F.A.哈耶克推崇的荷兰医生曼德维尔,在一篇经典的《蜜蜂的寓言》中指出:人的“自利主义”(自我保存)的行为结果,恰恰正是社会的繁荣(与他人共存)。由此可以发现,人的“自利主义”及“与他人共存”,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性,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对“人的自利主义”或“经济人假设”的单方面推崇,一下子就腰斩了格老秀斯对完整人性的真知灼见——排斥了人性中人必须“与他人共存”的一面。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经济学的古典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继承了格老秀斯对人性的剖析,也接受了曼德维尔的重大发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离开无数人的相互共存,完全无法想像。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失误就在于仅保存人性“自我保存”的这一面,却忽略了“与他人共存”是人性的另一面。
人的“自我保存”的天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亚当.斯密深知人“与他人共存”,如同“人的自我保存”一样重要,所以他的《道德情操论》的问世,先于《国富论》的问世。有些欧美经济学家不明白上面的道理,仅看到“人的自我保存”同“与他人共存”之间的冲突,就轻率提出一个“斯密悖论”。殊不知斯密对自己的定位,也首先是作为道德哲学家立足于世,显示出这位经济学之父对于“人必须与他人共存”的深度认知。苏格兰启蒙运动出于对“与他人共存”所作的探索,在道德哲学领域作出伟大贡献。顺便指出,基督教对于人应当“与他人共存”的指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没有基督教新教,人的自由权无法保障,更惶论“与他人共存”。片面强调“人的自利主义”或“经济人假设”,无视或拒绝“与他人共存”的法则,是对市场自由的挑战,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
市场的成熟与完善,是化解人的“自我保存”同“与他人共存”之间冲突的更重要的方面。因为人类社会每一个体要想“与他人共存”,只能借助市场实现。市场的神奇,也许我们至今尚未完全看透彻。1958年发表在《自由人》上的一篇《铅笔的故事》(作者Leonard E.Read),令无数杰出经济学家心悦诚服。这篇文章说的正是无数的人相互共存,并以一支铅笔的口气告诉人们,人究竟是怎样“与他人共存”的?铅笔自叙:成千上万的人共同投入铅笔制作的过程中,而他们压根儿不明白自己在“与他人共存”。他们中有伐木工、运输工、采矿工、冶炼工、面包师、服装师、食品与咖啡的种植工、餐具与茶杯的制造工、发动机制造工、汽车与火车制造工……他们之间互不认识,没人强迫或要求他们:你必须“与他人共存”,他们不明白自己与他人都在为制造铅笔而努力。他们不仅践行着“与他人共存”的法则,而且还不知不觉相互合作。“合作”是“与他人共存”的更高级形式。是谁指引他们相互共存,是谁指引他们共同合作?是市场!是市场的那只“不见你的手”!
新古典经济学没看到人性中“必须与他人共存”的一面,一味强调人的自利主义与“经济人假设”,结果只看到人的竞争,或者是“完全竞争”,或者是“不完全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无视“与他人共存”的自然法则,当然也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合作,这种竞争必然走向“恶性竞争”。要知道只有市场才能把人的“自我保存”的天性,与人们“相互共存”的天性融合在一起,使得每个人在为自己生存而努力时,也为整个社会作出贡献。旧俄时代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人性把人分成四等,一等人在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利己也利人;二等人利己但不损人,这是人的底线;三等人相当于畜生,他们只知利己而不惜损人;最后一等连畜生都不如——他们专门损人,最终又逃不出害己的结局。
在欧美世界,由于民众对基督教信仰早已根深蒂固,加上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下,私有财产权在市场运作中获得天经地义的保护,使得经济学的这一缺陷——对“经济人假设”的片面强调,没有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但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社会里,后果就不一样了。尤其在罪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共产分子以阶级斗争的旗号,公开洗窃城乡私有财产,彻底推倒与“他人共存”的法则。太子党与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更是到了疯狂的程度。此时经济学的课堂上再公开舍弃人性中“必须与他人共存”的一面,把“经济人假设”或“人的自利主义”视为经济学的基础,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缺陷,对共产分子而言,可谓正中下怀。大批的共产分子,他们口头崇尚集体主义,其实内心极端自私不惜损人利己。共产分子的头脑里,压根儿就没有“与他人共存”的意识。即便今日是“亲密战友”,也许明天就成了“阶级敌人”。除了公开的掠夺与欺骗,共产分子们还竭尽全力阻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形成,结果也就阻止了人们相互间通过市场实现合作。市场的自由探索与合作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社会成员无法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下自由求索与合作,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被激发出来,人与人之间也就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斗争或无法无天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斗争在毛时代,崇尚“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从1949年起直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大面积恶性内斗,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这笔账至今尚未清算。邓小平把毛的恶性斗争衍变为恶性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下,举国上下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这类恶性竞争的参与者。除了太子党与权贵阶层疯狂的巧取豪夺,只要看无数的建筑物、桥梁与高架道路,在承包建造时的层层盘剥、偷工减料;无数食品生产中,各种各样有害的添加剂任意投入;粮食、蔬菜与其他农作物生产中,各种转基因食品泛滥,各种有毒化肥滥施全然不受制约;房市与股市全是十足的寻租场,只有小红粉还蒙在鼓里;整个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触目皆是,就连佛门和尚也早已背叛了“慈悲为本”的信条,他们精于寻租骗钱,狂嫖乱淫且乐此不疲。所谓大国崛起,其实就是权贵阶层的财富崛起……中共特色的极端自利主义引发的恶性竞争,正使得这个民族不断陷于沉沦。
今天,人们已看得越来越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人性划分的四种类别中,共产分子绝大多数可以划入第三类——只顾利己而不惜损人,高层的共产分子除了专门损人,最终也逃不出害己的结局,这样的例子自8964以来不胜枚举。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片面强调,到共产分子无处不在的巧取豪夺,其中内在逻辑是否已彰显?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6/n140491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