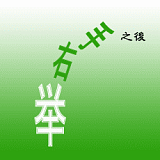我是读研究生回到了北京。那时文学批评专业的研究生比较少,“六四”学运开始后,我们导师非常明确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写历史的(尽可能地,因为你们这个专业),而不要去创造历史”,但是肯定是忍不住热血沸腾,我们要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去。
集会,声援,发表观点与当时社会的诉求,“反贪污反官倒⋯⋯”。
那个时候文学界有著名作家,如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他也与文学界的同仁扛着大旗前往天安门广场。“六四”结束之后他也受到了影响,丢了主编职位。
一个著名的诗人,写了一首歌,“我们走在火热的五月里,我们英勇地走上街头⋯⋯”我们唱着这首歌上天安门广场去声援静坐的大学生。
我们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集中在一片,我们同学都是声援者。我们老师坚决不让参加“高自联”,他说你们去声援、发表演讲都可以。一是不让静坐,第二不要加入大学生联合会。
到五月十几号开始,外地大学纷纷往北京走,声援北京大学生的游行示威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静坐请愿。外省来的,当时也有加入绝食静坐的大学生。
六月三号下午五点多,我与几名同学,从前门地铁站返回学校时,刚要出示学生证(那段时间无论公交车还是地铁,只要看见校徽,或学生证就不用买票),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对我们说,“不要拿了,不要拿。”她一看我们三个年轻学生就把我们叫过去,低声告诉我们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了,你们能回的就尽快回去。”我问,“怎么了?”她说,“今天晚上要戒严!”
其实我们对戒严这个词不太懂,完全是啥都没概念,今天晚上戒严,我以为就是包围起来了。
因为我们那一年级几个同学到军队驻地去实习与采风,感受军队生活,刚好是在总后学院。一开春、一开学就去了,跟部队接触很紧密。5月23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恰好在那个里面开的,来了五十几辆特别的轿车,之后学院整个警戒了,校外都警戒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不懂嘛。
回去草草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八点多快九点就走到了翠微路口,现在叫西长安街,那时候西长安街没有那么长,就是翠微路那边,军车、装甲车、坦克轰轰轰轰地就从西边一路往向天安门开。
我们三个同学就跟着军车,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阜新桥、西单,就快要到了新华门,西单电报大楼附近就听到了机枪“哒哒哒哒哒⋯⋯”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枪声,之前看电影知道子弹离人近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最近处的子弹声是“啾啾——啾啾”。一个年纪大的老伯大喊:卧倒!卧倒!我们在电报大楼对面的一个胡同里应声卧倒,人多得不行,后边有人趴在我身上,我趴在别人的身上。
我穿着一个白衬衣,小黑的碎花,一天就没低头看自己身上,没有注意。从戒严区往外走就要走出戒严线时,同学看见了,“他们三个活着,出来了!”有个同学看到我肚子上一片暗红红色,都是僵硬了的血,“你中弹了吗?你肚子上都是血!”当时我吓得都手抖,把衣服撩起来,一看肚皮光光的。回头一想,就是卧倒时,不知谁中弹了,我是染了别人的血。
因为我们没能走到天安门广场,到了新华门西边,机关枪响声不断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向里走了,是第一层戒严,我们是在二层里边,周围的群众让我们该回家快回家,我们就往外走,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艰难地走到上午九点多,到复(阜)兴医院。刚好在西二环这个边上有一个小医院,当走进门诊大厅里边,摆满了死人,我们刚开始数,数过去,就数了五十多具尸体,一回头,哇,摆满了,数不过来了,他们(共产党)硬说没死人,那一个早晨哪里来的这么多死人?
刚开始我们看着尸体很害怕,当数了一圈又一圈后,哇,我们后边全堆满了,一个一个摆着那里。这个时候一下不害怕了,那尸体各种形状,有大量的血,分辨不出来身份,有年轻的,也有中年人,有些模糊。
我还见证了军车上下来的军人对着围观群众开枪,装甲车、坦克是怎么样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我们一路跟着,亲眼见证了那段令人恐怖的历史。
只要共产党利益受到影响,它们对谁不开枪呢?因为毛老贼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把枪杆子牢牢抓在他们手里,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肆意践踏与蹂躏。
“六四”,如今人们都说是纪念,我认为六四是开始,至今还在进行中,直至让共产党彻底灭亡,并从中国那片土地上消失,从人类中彻底消失,“六四”的使命才能算结束。因此,“六四”不是一个纪念日,而是一直在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进行中的运动。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6/1/n1426216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