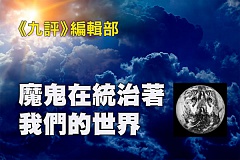从版图、山河、土地、河流、森林、矿、粮地、房子、积蓄,各种丰富的物资到人,从物质到精神,古老的中华民族被掠夺殆尽。
像是蝗虫过境,古老黄土地上一切物资被蚕食得一干二净。
以这全方位的国土大掠夺为背景,生存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华民族自身也遭遇了最深层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大掠夺。
在残酷而隐匿的心理背景下,古老的黄土地上出现了惊心动魄的自杀潮,同时出现了艺术和精神上的自戕。
(接上文)
世纪大掠夺
我们已述及70年来这西来幽灵对国土的掠夺盗卖,导致版图从饱满的秋海棠变成瘦公鸡(〈被遗忘的百年历史I〉)。而对于没有被盗卖的土地,这外来的政权一样造成了叫人扼腕的巨伤。就像树木、河流,甚至一座山一样,土地也会死亡。被土石流、沙漠化、水泥、毒水、无度砍伐斫伤的土地也会不可挽回的失去生机,一点一点死去。
神州大地环境污染严重,已濒临生态崩溃边缘。在《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作者郑义表示中国水土流失问题已达到超饱和状态,所有能够流失的土地已全部流失。2019年,中国水土流失面积达271.08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面积的28%,其中以西部最为严重(中国水利部数据)。2013年,由海内外环境专家小组及亚洲开发银行专家合力完成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表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卫空气品质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
此外,全国各地空气、湖泊、河流、地下水质都受到严重污染。依据官方数据,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经济总产值十分之一。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7条主要江河,四分之一受到严重污染,毒性之大能直接伤害皮肤。(《卫报》引用大陆2007数据)
看不见的地下水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然而依据中国水利部调查,2013年受测井中的地下水,超过80%受工农业排水严重污染,地下水只有3%清洁。专家认为中国地下水污染严重,重金属治理需要1000年。(日经商业出版社)
我们没有忘记,西来共产幽灵意图从精神到物质全面毁灭中华民族。在物质层面上,它已完成了摧毁神州大地地下水源,夺去了中华民族可食用的水——人生存的基本元素。
和水、空气一样,大自然中遍在的树木是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不可或缺、来自于老天的礼物。繁茂的绿色树叶能呼吸,是调节二氧化碳的功臣,而探入地下盘根错节的树根护持水土,坚固人脚下站立的土地。然而在中国,人迹所及之处,森林早已砍光。
1993年,中国林业部指出:经数十年乱砍滥伐,中国大陆的成材几乎完全砍伐殆尽。1997年,阿坝州林管局宣布四川已没有可砍伐的森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14名专家组成的队伍在中国河流源头探索。他们的足迹到了长江支流金沙江、大渡河,却没有看见森林。他们继续寻索,来到了长江第一大支流雅砻江。“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州,已抵达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在长江上游三大干支流中,金沙江、大渡河两岸的森林已基本砍光,唯有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雅砻江尚有残存。”
然而专家组千里跋涉来到了这里,却没找到森林。他们找到的是森林的遗骸。(郑义《中国之毁灭》)
在各种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是人们最容易察觉、直接亲身感受到的污染。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阴霾是空气污染最突出的表征。在冬天,国土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浓重有毒的阴霾覆盖,人们行走在路上,伸手不见五指,脸上戴着防毒面具一般的护罩,在烟雾弥漫中如同鬼魅。
世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资料,中国年新增病例380.4万例、死亡病例229.6万例,占据了癌症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全球双榜首。同时,中国新发癌症人数约占全球四分之一。全球每100名癌症患者中,21人是中国人,每天平均有超过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7人患癌。空气污染导致中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20%人口,却有全球约37%的肺癌患者。
为了经济起飞,全体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是全国人民。确切的说,是失陷的神州大地上被绑架的中华民族。而在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中,受害最严重的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
在被城市拒绝的各种有毒工厂大举入侵下,当代农村有三大悲剧:“致癌”、“致畸”、“致突变”,都是源自于空气、水、土壤严重污染。“癌症村”最早在河南被报导,现在安徽、四川、广东、黑龙江、山东、浙江等地都已复制了一整村农民大量集体罹患癌症的悲惨现象。
在“崛起”的中国,“癌症村”遍布全国,专家估计多达459个。这些死亡之村多散布在河流两岸,多是由于化工厂、垃圾处理厂、矿山等污染了水源、耕地和空气,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生活在癌症村中的农民从罹癌死亡人数到比率都在快速增加。在以超限速度崛起,市场化的极权中国,原先被应许了“解放”和土地的九亿农民,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了巨大代价。
唯物论的共产党对于人的掠夺罄竹难书。就是对人在物质上的掠夺也超乎想像。我们已述及国家机器对于良心犯器官的大规模盗卖(《被遗忘的百年历史VI》),这是对人肉体冷血的全面掠夺。中国共产党不但超英赶美,并且远远超越苏联老大哥,把唯物论进行到底,把人彻底物质化。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西来幽灵以金币和赤裸裸的权色刺激人最原始的欲望,把14亿人民往腐败的沟豁里拽。而在人民逐渐进入小康,有些积蓄之后,极权中国开始了割韭菜行动。在政府的策划下,先是成立千万投资平台,把稍有积蓄的中产阶级囊中的人民币吸金一样吸入,而后没有预警的把平台关闭,把人民一辈子的血汗钱残酷收割,造成大量受害的中产阶级自杀。也就是说,在屠杀戕害了地主、富商、将士、知识分子、工人、农人之后,西来幽灵把镰刀探向了中产阶级,这红色中国新兴的阶级。
共产幽灵把神州大地上所有能掠夺的物质,能掠夺的人掠夺之后换成海量的货币向世界砸下去,夺得了它觊觎的话语权。
到这里我们看出来:中心之国被共产阵营纳入囊中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邪恶阴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她广大的人口、丰富的资源,是邪恶占有世界的必要资源。共产主义依附在这庞大的文明古国身上,掠夺了她所有能掠夺的资源和人之后,从她身上辐射出去,一寸一寸侵蚀世界。
自戕
以这全方位的国土大掠夺为背景,生存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华民族自身也遭遇了最深层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大掠夺。在物资的掠夺之外,对于人的精神的掠夺抵达了空前的冷酷。1949年以来,历次运动中一次次对人的心灵施加非人的凌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基因突变,出现了毛所企图塑造的“新人类”。对于仁义的遗忘和由于传统的挪用变形,被绑架的中国人远远地偏离了自己的根源,失去了可以依循的精神和心理支柱。在这致命的背景下,红色中国生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一个以遗忘来保护自己,连自己被洗脑都忘记了的民族还能恢复记忆吗?然而,即使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症的人也有自我求生的本能。在残酷而隐匿的心理背景下,古老的黄土地上出现了惊心动魄的自杀潮。这是一种对谎言最彻底的拒绝。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发生在中国的自杀潮,对于中华民族被囚禁了70年的心灵,我们可能会有更深一层的体悟。
大规模自杀的人民和节节攀升的GDP以及不断扩张的向外输出形成了极度嘲讽,冰与火的对比。2009年,中国每10万人中有22.23人自杀,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红色中国自杀人口都居全世界前列。(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近年来,红色中国的自杀群体中多了两个怵目惊心的群体。绝望的农村老人如染上传染病一样,把自杀作为自己的告别通道,以各种悲凉的方式默默自戕离世。对于他们的自绝离世,无论是他们的儿女或村人都视为理所当然,无需自责,更无需悲伤,甚至视之为一种正常的解脱途径。在一些家庭,人们甚至毫不隐藏的等待、逼迫老人死亡。也就是说,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非正常现象——更准确的说,这是被合理化的非正常状态。在红色中国诸多变异的病症中,多了农村老人自杀的悲惨之症。
在这现象出现之前,我们看见一座座被抛弃的农村中是废墟一般的粮地,和垃圾场混在一起的农田,被挖土机一寸寸刨起来、变成有毒工厂的良田。我们看见弃守在被年轻人抛弃的农村中,一身瘦弱,衣衫单薄的老人以手抹泪,悲苦的说:“老人没用。”这是在改革开放前期。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当年站在被抛弃的农村路上,抹泪悲苦的老人集体以这最悲惨的方式离去,结束自己“无用”的生涯。在传统中国,安享晚年,儿孙弄膝,备受尊敬的老人到了红色中国,成了没人要、废物一般的干柴,只有以自戕结束没有荣耀、没有尊严的生命。
在老人的另一端,越来越多青少年轻生。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纵身跳下楼,在一瞬间从这世界消失。英国《经济学人》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一。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每1分钟就有2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中国北医儿童发展中心)
这些幼小的生命承受教育体制下过重的压力。以冰冷的分数、成绩来衡量人的生命造成的压力,使得中国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比例相当高。同时,近年来整体社会把人的数据化管理形成了不适合于孩子们生长的,异化、反人性的环境。社会信用体系施行没有几年,这把人数据化、物品化管控的冷血方式就已向下流泻,流入了孩子们脆弱易感的心灵,提前生出了致命的病变。趁着这异化人性的病变完全侵入身体前,为了保全自己的灵魂,孩子们纵身一跃。
自杀的不止是老人和小孩。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在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人们自戕的悲惨景象。无路可走的穷人、上访者、拆迁户自杀抗议的人每年都有好几起,访民集体喝农药自杀的也时有发生。在天安门,长期工作拿不到薪水的农民工集体跳金水桥,喝毒药,或悄悄爬到广场边上的高楼顶自杀。
不只是平民百姓,2000年之后,中共高官自杀数字成倍增加,2012年之后更出现自杀潮,各级高官:省长、市长、县长、院长、科长、校长;公检法各级领导:公安局局长、看守所、派出所所长、公安厅厅长各种自杀、被自杀的案子怵目惊心。在共产中国数十年来的体制性腐败下,伴随这些高官震慑人的官阶和财富,是如影随形的钱权色陷阱和他们不可避免的、致命的堕落。在红色中国巨大的隐形监狱中,这些狱卒、监长、狱长,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遭遇了各种不名誉而惨烈的死亡。自杀或被自杀成为他们共同的归宿。
这一现象其实是“新中国”成立后高层领导自杀、被杀的延续。从高岗、刘少奇、林彪到江青,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以各种叫人惊悚的方式被批判、受刑、消失。一旦进入共产党自动运转的机器,不论爬得多高,人毁于其中的命运就已定下。
就在极权中国向外扩张红色意识,攻城略地时,她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土上,千千万万人——包括年幼的下一代——以各种方式自戕离世。

在施行30年一胎化计划生育后,21世纪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也面临老龄化加剧的社会危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民政部部长李正恒《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0出生人口出现崩盘式下跌。同时,养老服务司司长俞建良在2020年提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提升至“国家战略”层次,显示中国人口危机十分严峻。
雪上加霜,作为过河卒子的孩子们患上感染病一般,纷纷退出这强把自己纳入囊中的“红色祖国”,提前退场,剩下人口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缺少金字塔底端的下一代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共产中国。
这种对于“祖国”生产力量的釜底抽薪,似乎是被集体绑架的中华民族的一种悲壮的复仇。没有任何别的武器,甚至连以笔为旗,或做公民记者报导事实,在互联网上抒发情绪的可能也被剥夺。这些古国人民选择了以自己的生命为最后的武器。死亡是他们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中国当代绘画中的自戕—— 沉痛的家族史
与这集体自戕平行的,是红色中国在艺术文化上的精神自戕。这种精神上的自戕来源于内在的病变,是肉身自戕的另一种形式。这种精神的自戕表现在绘画上尤其突出,是人们心灵诚实的记录表。
改革开放后,人们从社会主义极权话语的锁链解脱,一跃而入以超限速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及生猛的消费/后现代文化。在国家机器的大力推动下,出现了以经济取代一切的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的社会面貌。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后)共产中国出现了奇异的现代绘画。
在人的自戕之外,出现了艺术和精神上的自戕。89坦克之后,文化界从沉重的历史、社会责任转向。反美学成为一种时尚,理想和精神一起被抛入下水道,文学及艺术作品中洒遍了暴力、自戕、自弃的语言和意象。
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是如何进入21世纪。方力钧作于1999年的〈1999-12-31〉中,出现了一群没有眼睛,五官平面,布偶一般伸手盲目抓向空中飞舞四散的花瓣的,被戏称为“光头泼皮”的人。和方力钧其他画作一样,画上的人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没有个性、知觉,表情混沌似弱智者。国家机器大量制造出来的后现代螺丝钉。然而仔细看,我们看见了这些脸上茫茫然的,一丝又似痛苦又似欣喜,如白痴又如孩子的渴望。
1988年以来,方力钧开始光头人的创作。大小不一的木偶人出现在大画布上,模糊不清的五官挤弄出身不由己的表情。在蓝色调的〈打呵欠的人〉里,是一张嘴巴极力斜曲,变形的光头巨脸。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这由于无聊而变形的脸竟似一张发出愤怒嚎喊的面孔。
这是一种难以尽述的水火同源:在深受压抑的后极权社会,极度无聊和愤怒呐喊是同一枚铜板的两面。在这张巨脸后,是四名穿囚犯服/中山装,阴郁地走过的,猿人也似,影子也似的人。对这些已经自成系统的语言符号,批判者有各种解读:“一种自我嘲讽……对意义系统自我逃离的形象”(栗宪庭)、“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愤懑而挣扎的形象”(易英)、“剔除了历史负担、意义负担、价值负担、人文负担,在一片空白之下的‘空白之人’”(汪民安)。
对于自己荒诞不经的视觉话语,方的解释是出人意表的:“在我的潜意识中(光头)带有了一种叛逆或者调侃的意味。”“实际上我的作品是写生的作品……我所体会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当下这种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
对于这位创作者,这些出自梦魇的,缺乏主体重量的人物画像来自人们所生活的真实——来自于今天的中国。
当中国画家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下转而对当下的生活状态进行描述,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笔下将出现这样的写生群像。在新表现艺术中,有如和声对位一般,出现了各种异化的人的形象。这一集体镜像深化了这一“心理写生”的面向,使人难以忽视这群画家笔下叫人悸动的深度真实。与创作于1980年的〈父亲〉,罗中立以古典写实、大特写的造像风格来呈现农民的经典油画处于绝对化的两极,这些子辈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所塑造的脸孔使人忐忑难安。
在当代中国现代艺术的自戕中,人变为鬼魅。张晓刚的〈父女〉(2005),一如他这一系列名为〈血缘—大家庭〉的画作,以严厉的黑白油彩、拉长的比例把影像中的人物转化为幽灵。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画中人漆黑硕大,没有表情,一如扁平黑玻璃珠的眼瞳。这吸光,纯粹物质性的黑抹煞了万物之灵的灵性,连带抹除了画中人物的生命。比方力钧绘画中后现代螺丝钉的木偶面具更具有深度与耐人寻味的余韵,这是有着同一血缘的,具有历史渊源的幽灵玩偶。在这恐惧所统御的国度,人们分享同一张面孔。这些当代中国绘画中,人没有温度,没有实体。没有生命。一如一个个在真实生活中自杀的人们,在艺术中,人们如同行尸走肉,失去了温热的生命。
1993年,张晓刚画了第一张名为〈血缘〉的作品。在这之前,有六年的时间,他只画死亡。以60年代及70年代的家庭黑白照片为灵感,这些平涂、全无质感的画像上是各种组合,表情奇特或一无表情的家族,只有年幼的下一代脸上抹上了色彩。根据张晓刚自己的证词,他的创作企图“呈现假的照片”,也即是暗示隐藏在一张张照相馆千篇一律的照片中,人们深受压抑的心理状态。
“我要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他说:“在中国,有一个时期,每一个家庭看起来都一样。”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血缘”这一概念,随着画中牵延的,冰冷的红线,获得了不落言诠的歧义。这是一群不对命运抗议的,彼此血缘相系却又互为仇敌,无辜如羊羔的魂影。
绝非出于偶然,张晓刚和方力钧画笔下的人物有雷同的迷茫,更有病态的非精神性。更重要的是〈血缘——大家庭〉系列中这些冷漠的形象内在潜藏的复杂情感。他们同时是无辜如动物的受难者,巨大历史灾难的承担者,也是冷漠无知,缺乏内视能力的“非人”。是残忍的,也是温柔的。是自我放弃,也是庄严,无法诋毁的。是绝望的,也是渴慕的。正是由于他们永远处于这两极之间,形成了艺术持久的张力,使得我们在这些画前驻足,思索,悲痛难当。
在〈血缘——同志120号〉中,出现的是与大家庭系列一式一样的黑白脸孔,唯一不同的是由于这是独照,画中人的肃杀之气更为集中,而穿中山装的这位面无表情的同志,在“同志”这一字眼蕴含的所有意义之下,更让人心生畏惧。他身后沉郁如乌云遮蔽的背景富有强烈的暗示性,遥指那一段悲剧式的民族历史。
作为时代的心理镜像,这持续而相互呼应的新表现艺术裸露了文革以来中国人的存在困境。与方力钧的心理写生相呼应,张晓刚说:“生命的悲剧性和人心的孤独、惶恐对我来说就是现实。”
让我们想像一间挂满了〈血缘〉系列绘画的大房子,一幅幅走过去,直到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整代迷失困顿的灵魂,以及透过艺术而沉淀、凝结的孤独、悲凉。这一切赋予这些绘画难以承担的历史和人性的重量。似乎是,唯有通过这变异的绘画语言,方能贴近变异的人心。
我们不得不看见,后89新艺术潮流所呈现的中国人形象是缺乏感知与行动能力的,主体严重匮乏,失落的人的幻象。这一幻象和现实中纷纷自戕的人们平行,诉说着生活在红色中国的人们精神上的死亡。(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5/n1300176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