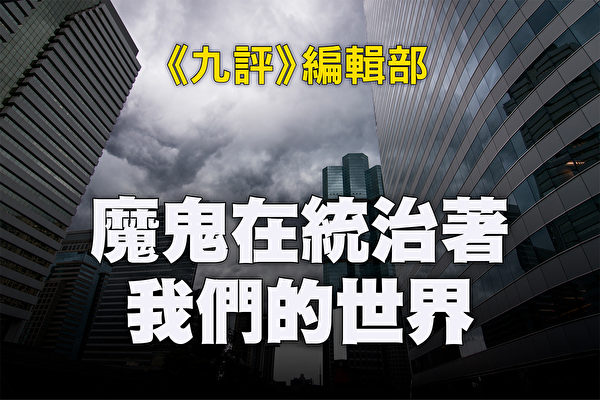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五章 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根源
目录
前言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结语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它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长布赖恩‧克洛兹尔(Brian Crozier)毕其一生研究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帮助反共阵营包括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等反共领袖分析、认清共产邪恶及其恐怖根源,发表了许多论文、著作,告诫世人共产主义乃是国家恐怖主义及非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5]
苏联格鲁乌(GRU,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鲁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苏联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日本突击队、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击队等等,后面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支持。[7]这些极端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袭击。1975年中情局驻雅典总监理查德‧莱尔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约统帅亚历山大‧黑格将军(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车队遭到炸弹袭击,黑格将军的三名保镖受伤;1981年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侥幸躲过一次火箭攻击。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对穆斯林国家输出革命给恐怖主义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东本来是英国和欧美国家的传统殖民地势力范围。随着民族独立,苏联借机挤进中东。但是,中东各个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争端、中东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国利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美苏冷战双方在中东的争夺、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切让中东的事态变得错综复杂。
而苏联对穆斯林地区的渗透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诡异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相信真主,而苏联的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而且是以消灭宗教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实,共产主义就如同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共产党就初试牛刀,1920年6月帮助在伊朗的吉兰省成立过一个苏维埃政权,叫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称吉兰苏维埃共和国)。在共和国境内展开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例如反宗教宣传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们的财富。因为很不得人心,该政权很短命,1921年9月就灭亡了。
在穆斯林地区,的确也出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一些穆斯林领袖在调和伊斯兰教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搞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还有埃及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苏联和中共支持,因为搞恐怖活动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中东的南也门、西亚的阿富汗等国都出现过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时期。前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区扶植起来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打了十年之后,苏联最终放弃了阿富汗。
事实证明,要在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重的地方推行共产主义并不容易。可以说,苏联在这些穆斯林地区的共产革命输出是很失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没有给该地区留下重大的政治遗产。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极端伊斯兰恐怖行动。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将,是前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秘书兼对外情报总局第一副局长、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顾问,也是前东欧投奔西方的最高级别官员。帕切帕在《俄国人的脚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产主义扶持中东恐怖主义的内幕。他引述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头子亚历山大‧萨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话说,“在今天的世界,当核武器使得武力过时了的时候,恐怖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里就发生了82起劫机事件,是由苏联克格勃及中共支持并资助的巴解组织干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萨克哈洛夫斯基的办公室,注意到墙上挂的世界地图上有一片插上小红旗的海洋,原来每一个小红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萨克哈洛夫斯基对帕切帕说:“劫机是我自己的发明。”在1968到1978年间,光是罗马尼亚的安全部门就给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周运送两架货机的军用物资。东德解体后的档案显示,在1983年,东德对外情报局就给黎巴嫩恐怖组织送去了价值1,877,600美元的AK-47冲锋枪弹药;捷克斯洛伐克给伊斯兰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吨的无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头子、后来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决定要发起一场精心策划而又隐蔽的宣传运动,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播下反犹和反美的仇恨种子。安德罗波夫被西方称为“新的造谣时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输仇恨,并将这种情感武器变成对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恐怖主义血腥屠杀,让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基地组织”登上了新闻头版。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风口。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恐怖袭击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边,共产党严厉钳制言论自由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场景。从互联网论坛、聊天室,到大学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对此欢呼:“干得好啊!”“强烈支持针对美国的正义行动”……根据中国主要网站“网易”对91,701人的调查,表达“强烈反对恐怖主义”的只占17.8%,多数人或者选择“反美”或者选择“好戏在后头”等幸灾乐祸的态度。[10]
这些为恐怖袭击欢呼的中国人和本‧拉登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表达出相似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来自同一个毒根的毒素,这个毒根就是共产邪灵。中国人受毒害,是因为从小在魔鬼的党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维框架思维。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中,是抗击共产主义苏联的,他的恐怖主义怎么会与共产主义沾上边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些本‧拉登们的恐怖主义思想来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号称“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11]“当代圣战组织教父”[12]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反恐专家、前美国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员威廉‧麦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声明他们的动机时常常引用库特布的教导,并把他们自己当作库特布衣钵的承传者。[13]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继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将库特布的思想看作是点燃了极端伊斯兰圣战运动之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表了中东问题专家汉森‧汉森的报告《伊斯兰国(ISIS)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和政治内涵》,在结尾处报告引述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的话来概括伊斯兰国的思想核心:“伊斯兰国由赛义德‧库特布规划蓝图,由阿卜杜拉‧阿扎姆传授,由奥撒玛‧本‧拉登将之全球化,由阿布‧奥玛实现,然后由巴格达迪执行。”[14]
本‧拉登们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国(ISIS)继承和发展了库特布的思想(当然还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这种思想通常被称作库特布主义。通俗地讲,库特布主义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旧世界”,鼓励“圣战者”不惜牺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奋斗到底,要“解放全人类”。[15]
这些“豪言壮语”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是的,因为库特布早年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烙印。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莱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库特布实际上曾经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联络人。[16]
库特布是埃及人,出生于1906年,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学习了社会主义和文学,在4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两年。[17]回到埃及后,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库特布与陆军中校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来。纳赛尔是“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领导人,该组织倾向社会主义。1952年,纳赛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说法是库特布和兄弟会同纳赛尔一起策划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政变。库特布希望纳赛尔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但是,纳赛尔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纳赛尔开始打压穆斯林兄弟会。于是,库特布的兄弟会准备暗杀纳赛尔。计划失败,库特布被指控谋杀入狱。在监狱的头三年,库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后来条件变得宽松,并允许他写作。他在狱中写了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在古兰经的阴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这两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古兰经、伊斯兰历史、埃及和西方的社会等问题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极端主义主张。库特布曾短暂获释出狱,但他拒绝出国,选择了再次入狱。1966年库特布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埃及纳塞尔总统的阴谋,被处以绞刑。
库特布的颠覆性思想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给予了新的诠释。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圣战(holy war)。其实在阿拉伯语中“吉哈德”本身是挣扎、抗争的意思。对主流穆斯林来说,它可以是内心的挣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敌(defensive jihad)。[18]库特布将之延伸为不受限制主动采取暴力的“圣战”。[19]库特布为暴力攻击“圣战”打下理论基础,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绞刑架为荣耀,亲身给追随者做了殉教榜样。
库特布的学说主张,任何遵从世俗法律的社会,或者遵从世俗道德的社会体制,就是非伊斯兰的“旧社会”──贾希利亚(jahiliya,意为对宗教真理的无知,原指伊斯兰教传播之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算自称穆斯林社会,也属于贾希利亚。实际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会体制就被他视为贾希利亚,应当被推翻。[20]
对库特布来说,这个“旧社会”(即贾希利亚)不仅是个体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获得并遵守伊斯兰价值观和法律的最大障碍。这个“旧社会”是强加给人的,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在“旧社会”的人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隶)。对奴隶(即被压迫者)而言,暴力的圣战是伊斯兰教允许的。库特布主张通过圣战“解放全人类”(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领袖认为库特布走得太远,他的书出版后被视为异端。[22]
库特布进一步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概念(即普通民众接受了统治者的“虚假意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他们没有主动的愿望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生活在贾希利亚中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和“压迫”,[23]也就不会主动起来参加圣战,“解放”自己。
“怎么办?”库特布从列宁那里找到了答案。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熟悉马列主义的学者在研究库特布的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锋队”(Vanguard)、国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这是典型的列宁主义用语。列宁在写作《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时,面临的局面和挑战,与库布特非常类似。列宁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Proletarian vanguard),库特布照搬了这套理论,只是把无产阶级换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
列宁非常强调组织和先锋队的作用,他区分了自发性与自觉性,提出了“建党理论”。他认为如仅仅依靠自发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涨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等肤浅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的所谓“觉悟”。列宁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进分子”(往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他们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条件)对工人进行煽动和灌输,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觉悟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了发挥这一部分“先进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把他们的生活全包下来,为他们创造秘密工作的条件,使他们成为全职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政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4]
美国海军研究院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圣战主义思想家们没有直接引用列宁作为其思想启蒙,但二者的概念、逻辑,尤其是赛义德‧库特布泄露出其[列宁]影响。20世纪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库特布肯定阅读过列宁的作品。库特布有两个关键概念直接来自列宁: jama’a(先锋队)和manhaj(纲领)。”[25]
库特布从列宁主义里学到的“精髓”,就是要组织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锋队。库特布的理想,几乎就是列宁的理想。
罗宾逊教授阐述道:“库特布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宁]一模一样的论断,大多数的穆斯林沉迷于腐化体系的非正义的和反伊斯兰的统治,所以不知道怎样才能起来拿起武器反抗,一个专业受训的圣战先锋队必须组织起来针对国家机器反抗。”[26]此外,“列宁坚持先锋队的核心,是有一个详细与周密协调的纲领,然后具体实施革命。在库特布的书中也有相似的伊斯兰版本。”[27]
对库特布来说,这一支他认为的“真正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就要担当其拯救伊斯兰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锋队要去打击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虚伪者”,要按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去做,建立一个基于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新国家,并用暴力把伊斯兰带到全世界。
除了先锋队,库特布的学说里也有社会平等、消灭阶级、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类”的内容。[28]这些内容,都会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
库特布死后,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继续出版塞义德‧库特布的书。在1993年出版的库特布的书“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库特布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该书第61页中,库特布直白表示,伊斯兰教“是一个独特的、建设性的、实证主义的教义,它是由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并增加了它们的和谐、平衡和正义。”[29] (方括号内是本书作者加入的内容,便于读者理解。)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在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时,有学者还指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煽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这种矛盾上升为不可调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决的矛盾。伊斯兰极端主义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策略。想想看,炸毁曼哈顿的世贸大楼就能实现库特布的伊斯兰大同世界了吗?当然不会。极端主义为的是制造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加剧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对穆斯林的仇恨,然后用这种仇恨来煽动更多的穆斯林起来仇恨西方。[30]这就是与马克思列宁宣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样,一定要让这个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才有机会发动革命。共产主义这么想,受其影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这么想的。
不夸张地说,库特布的学说更接近共产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义。虽然从宗教上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却吸取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学者这样指出恐怖主义的实质:和自由世界对抗的真正敌人还是共产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穿了件传统伊斯兰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运动使左派思想广泛传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倾向暴力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芬兰政治历史学者安特洛‧莱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认为,现代恐怖主义诞生于1966~1967年,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把基于穆斯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学生运动中,许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来观念带回去,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32]
开罗的美国大学媒体研究教授施莱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经见过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当时正在开罗大学学医的扎瓦希里对施莱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在精英学院──医学和工程学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莱弗对此并不奇怪,他回答说,在60年代,这些院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据点。他指出,伊斯兰主义运动只是(60年代)学生反叛的最新发展趋势。施莱弗回忆说,“我说,‘听着,艾曼,我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你说话时,我觉得我回到了党内。我不觉得自己好像和传统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法西斯联系起来,而出于某种理由不愿提及共产主义根源。其实,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也没有专门的宗教信仰基础。从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全人类观和宗教情结来说,极端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渊源更为紧密。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库特布的著作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学者、后来的基地组织创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中阐述了库特布对本‧拉登的世界观的影响,并直接将阿扎姆称为库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和追随者来传递影响,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穆罕穆德‧库特布后来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兰的教授,同时也负责编辑、出版和推广其兄长的学说。
本‧拉登在学生时代就读库特布的书,本人也与穆罕穆德‧库特布熟悉,定期参加后者在一间大学里的每周的公开讲座。前中央情报局负责本‧拉登小组的官员、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儿(Michael Scheuer)直接称库特布为本‧拉登的导师。[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赛义德‧库特布的狂热追随者。[37]扎瓦希里少年时代就从他叔叔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库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监狱中忍受磨难的“伟大”。[38]库特布死后,扎瓦希里在回忆录中写道:“纳赛尔政权认为处决赛义德‧库特布及其同志们使[极端]伊斯兰主义运动受到了致命打击。”“但表面的看似宁静却隐藏了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发酵以及埃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核心的形成。”[39]库特布被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参与组建了一个地下激进组织,决心“实现库特布的理想”。[40]这一年他15岁。此后扎瓦希里参加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后来成了本‧拉登的导师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本‧拉登被击毙后,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组织的头目。
上文引述过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库特布是最重要的强调暴力圣战的思想家。[41]几乎所有的逊尼派圣战组织的概念和思想创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库特布的书中找到。[42]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圣战组织,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兰旗号下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纲领。[43]
1981年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组织盖码‧伊斯兰米亚(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纪90年代其针对政府官员、世俗知识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游者发动袭击)等都奉行库特布主义。[44]
奉行库特布主义的激进圣战组织也被归类为萨拉非圣战组织。拉特洛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将库特布称作萨拉非圣战主义之父、伊斯兰国的开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兰国的大脑──ISIS及其哈里发意识形态》中写道:“五十年过去了,赛义德‧库特布被处死刑成就了萨拉非圣战主义的传统,成就了伊斯兰国的思想。未来没有里程碑了,我们已经到达地狱的入口。”[46]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持续的威胁──基地组织和其它萨拉非圣战者》中概述了库特布对萨拉非圣战主义的影响,同时列举了40多个萨拉非圣战主义组织,影响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纵观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各种组织,它们之间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采用库特布的主动进击型“圣战”去做斗争,成为了库特布的衣钵传人,也成为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美国政府国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可以确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案件的伤亡者中,过去五年内82%至97%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国国务院在2016年的报告中说,2016年发生了11,072起恐怖袭击,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袭击的肇事者)。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发生在104个国家,但它们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发生在5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49]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国家。
相比而言,恐怖袭击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于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从1975年到2015年,外国出生的恐怖主义造成了大约3,024名美国人死亡(这一数字还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约有74名美国人。
极端恐怖组织虽然最乐于打起伊斯兰旗号,但最终被其伤害最大的实际上是穆斯林社会。对于恐怖主义背后的魔鬼来说,打什么旗号都不重要,通过各种手段毁灭人类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已有几十年历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国认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导。人们知道本‧拉登主导策划劫持客机发动9·11袭击,但劫持客机的首创者却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阿拉法特从1959年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国,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种武装组织的主要头领。整个中东地区最得宠于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属。他曾十四次造访中国,几乎会见了历届中共党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深得中共赏识。其在恐怖袭击中屡屡得手,又游刃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风光一时。
1964年,阿拉法特组建了法塔赫武装恐怖组织“暴风”突击队后,马上到北京与周恩来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恩来当时就指点他: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提诸如“把以色列赶入大海”之类的口号,因为这类口号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斗争。[51]
中共对这个恐怖主义小老弟除军火、经援之外,屡授机宜,指点其如何与美国、以色列等国交战,及如何扩展国际影响等,还特邀巴勒斯坦人员到中国学习、接受培训。向中共老大哥“取经”回来后,1965年1月开始,阿拉法特就以游击队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对以色列开战。1965年5月,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PLO)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共破格承认该办事处享有外交机构待遇,并在国际外交各种场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中共立即予以承认,并于同年11月20日与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间,阿拉法特和中共党魁江泽民互访见面。期间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幕后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国抗衡,使得中东地区战火不断。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从事各种公开的、地下的军事恐怖行动,声称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产国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它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员,也是“欧洲社会党”(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观察员”。
美国、以色列一直认为阿拉法特是中东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所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组织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划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侯赛因国王幸免于难。[53]同年9月,法塔赫连续劫持英国、德国和瑞士三民航客机并在电视摄像机前摧毁三架劫持的国际班机,在国际上造成轰动。恐怖分子称:“我们劫持一架飞机远比我们在战斗中杀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为其后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开了先例。后几十年里劫持民航飞机成了恐怖分子的一个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属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组织制造了一起进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袭击事件。而策划、实施这一起恐袭事件的阿布‧哈桑‧萨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恐怖分子在德国慕尼黑正在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竞赛的奥运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开枪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同时,还射杀了一名德国警察。[55]几十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滥杀无辜平民,阿拉法特对首开对平民的恐袭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中共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由来已久,并一直和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约300名军事顾问到当时阿富汗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训练基地外,还在新疆喀什及和阗增开军事训练营,教他们使用武器、爆破、战斗策略、宣传技巧与间谍战等。新疆成为训练阿富汗圣战组织与苏联作战的基地。到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中共军队至少训练了几千圣战分子,为他们提供价值2亿~4亿美金的机枪、火箭发射器以及地对空导弹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权后,包括其庇护本‧拉登基地组织期间,中共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保持了密切关系。虽然基地组织对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实施恐怖袭击,而塔利班拒绝向联合国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对联合国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袭击基地组织,中共花一千万美元向基地组织购买未爆炸的美国导弹,以改进自身的巡航导弹能力。[57]同时,中共继续向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58]2000年底,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关闭本‧拉登在其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但中共投的是弃权票。在那之后,中共继续与塔利班秘密商谈,并达成协议由华为帮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广泛的军用通讯系统。[59]就在9·11恐怖袭击的当天,中共与塔利班官员签署了扩大经济与科技合作的协议。[60]
更令人震惊的是,“9·11”发生后,两个中共军人被称为英雄,因为他们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战》一书,里面提到“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攻击,对美国而言将会很棘手”,他们还明确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团组织这场攻击行动”。[61]可以说,中共的“超限战”理论是本‧拉登发展恐怖袭击这一手段的理论指导,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诸实践。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对塔利班政权进行制裁时,中共不光投弃权票,而且在美军开始空袭塔利班目标后,仍派出军事人员帮助塔利班政权。9·11事件后,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共军方的中兴和华为在帮助塔利班军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一个电话网路。[62]
2004年中,据透露,中共情报机构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帮助本‧拉登筹募运作所需的资金并洗钱。[63]
随着柏林墙倒塌,暴力共产主义阵营面临土崩瓦解,中共继承前苏联的衣钵,不得不独立支撑面对自由世界的强大压力。正当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谴责共产主义暴政时,“9·11”恐袭发生,世界格局随之大变,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全方位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其实,这正是共产邪灵为了转移视线,让中共残喘并坐大的伎俩。在西方为反恐疲于奔波的时候,一场中美之间的财富大转移悄悄发生了,共产邪灵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共产主义。
每当世界反共阵营开始围剿世间共产势力时,共产邪灵往往就会指使恐怖组织肇事,让人们无暇顾及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邪党及其毁灭人类的运作,忙于和恐怖组织交战,并花大力气反恐、防恐,却把人世间正邪交战的主要战事搁置一边不顾。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位德国音乐家如是断言。他评价的不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9·11恐怖袭击。[64]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在第一时间为恐怖分子欢呼、辩护和洗脱罪责。一位美国作家夸赞恐怖分子“绝顶聪明”,在他眼里袭击有情可原,因为“美国历史上做错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别塔[指世贸中心大楼],因此大楼必须被摧毁”。一位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其中打滚的经济体每年用贫困杀害上千万人,纽约就算死了两万人又怎样?”[65]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难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魁之一)。[66]
为了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武,各种激进左派势力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语言学家、激进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计划在阿富汗发起“悄无声息的群体灭绝(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发起“和平守夜”和抗议集会(teach-in)。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乔姆斯基到接近战区的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个星期,向上百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谣言。他说,美国计划用饥饿的方式杀害三四百万阿富汗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9·11”的凶恶和残暴。[67]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说他希望美军经历“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之战”。[68]摩加迪沙之战指的是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的基地组织袭击美军的事件,18名美国士兵死于这一伏击。激进左派发起的反战运动针对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是在拉自由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后腿,客观上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内应。
在2003年2月,在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个月之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录音,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美军,要在巷战中重创美军,里面公开声称“穆斯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在反战上是一致的”,向反战的左派组织发出动员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个反战组织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这是一个典型的左派激进组织,成员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左派或者进步主义者。其主要组织者很多都与“国际行动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有关。“工人世界党”是美国的一个极端的共产党组织(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实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沿部队。参加反战的还有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产党是和中共有联系的马列主义政党。[70]
除了积极为恐怖分子开脱、组织参与反战运动以外,法律界的激进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对“9·11”之后不久国会通过的旨在增强美国反恐能力的《爱国者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联邦调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为恐怖分子提供资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归案。如果有爱国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归案,也许可以避免9·11袭击。[71]
策划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其辩护律师林‧斯图亚特(Lynne Stewart)借着到监狱里探望拉曼的机会,替后者传递信息给其中东的追随者,告诉他们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斯图亚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惊讶的是,在她的有罪判决之后,斯图亚特反而成为左派的政治偶像,屡屡被邀请到大学、法学院及其它集会演讲。[72]
美国学者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恶联盟:激进伊斯兰教与美国左翼》 ,揭示了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美国激进左派之间危险的关联。他通过分析指出,国际激进左翼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边防战士。[73]
为什么西方激进左翼愿意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西方民主国家?西方激进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为了从内部摧毁西方文明不遗余力,所有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都成为他们联合的对象。虽然左派意识形态在表面上和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冰炭不容,但由于两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标,因此结成了危险的反对西方文明的联盟。由于同样原因,两者都成了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得力工具。
结语
从巴黎公社、列宁的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把恐怖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在共产国家之外,共产邪灵在不同时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为其实现恐怖主义目的之工具,包括运用恐怖分子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势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随着科技发展,没有道德约束的恐怖分子越来越容易运用各种手段来制造恐怖,人类时刻处于他们的威胁之下。
恐怖主义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惧来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类普世价值的,要达到的目的是邪恶的。这些核心理念与共产主义同根同源。可以说,共产邪恶因素为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深层的邪恶价值的支撑点,为他们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恐怖主义最大的牺牲群体往往都是那些产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国家,虽然见诸报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对西方的袭击,而被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残杀的最大牺牲群体却是穆斯林。这一点同共产主义残杀的一亿多人几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谓同出一辙。
恐怖主义带来了暴力、仇恨、残杀、恐惧、废墟和悲剧,其受害者是全人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密不可分。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同时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义,因此,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恐怖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才是对人类的根本威胁。不把恐怖主义的毒根拔掉,世无宁日。认清共产邪灵是人世间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边,走回神为人留下的传统的正路,邪灵才无法利用人类达到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
[1] Brian Whitaker,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The Guardian, May 7, 2001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may/07/terrorism.
[2] “Lenin and the Use of Terror,” World Future Fund,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wffmaster/Reading/Quotes/leninkeyquotes.htm.
[3]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1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19/terrcomm/index.htm.
[4] Carey Goldberg, “‘Red Saturday’ Not Such a Celebration for Lenin,”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1, 1990,https://apnews.com/0f88bdb24ea112b606c9c56bca69e9dd; Francis X. Clines, “Upheaval in the East; Soviet Congress Debates New Presid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03/13/world/upheaval-in-the-east-soviet-congress-debates-new-presidency.html.
[5] Brian Crozi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Rocklin, CA: Prima Lifestyles, 2000).
[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8), 80.
[7] “The KGB’s Terrorist Footprint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198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1/09/23/the-kgbs-terrorist-footprints/16f129fd-40d7-4222-975c-6e39044768bf/?utm_term=.0f15a9d808da.
[8] Ion Mihai Pacepa, “Russian Footprints,”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4, 200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06/08/russian-footprints-ion-mihai-pacepa/.
[9]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33.
[10] 〈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国内言论摘登〉,《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5-mcs-2001-issue-4/596-911.html。
[11]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12] Raymond Ibrahim, “Ayman Zawahiri and Egypt: A Trip Through Time,“ The Investigative Project on Terrorism: A Special Report, November 30, 2012, https://www.investigativeproject.org/3831/ayman-zawahiri-and-egypt-a-trip-through-time.
[13] Quoted in Dale C. Eikmeier, “Qutbism: An Ideology of Islamic-Fascism,” Parameters (Spring 2007), 85–98, http://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parameters/Articles/07spring/eikmeier.pdf.
[14] 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_253_Hassan_Islamic_State.pdf.
[15]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16] Robert R. Reilly, The Roots of Islamist Ideolog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06), 4, http://crce.org.uk/briefings/islamistroots.pdf.
[17]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1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19]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logy#gsc.tab=0.
[20]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1]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logy#gsc.tab=0
[22]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3] Roxanne L. Euben, “Mapping Modernities, ‘Islamic’ and ‘”Western’,” in Border Crossings: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ed. Fred Reinhard Dallmay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20.
[24] Vladimir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Trans. Joe Fineberg and George Hanna,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
[25]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John Arquilla and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9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9] 该书原文为阿拉伯文,在许多穆斯林网站可以查到引述段落的英文翻译和阿拉伯原文图片,如“Impaling Leninist Qutbi Doubts: Shaykh Ibn Jibreen Makes Takfir Upon (Declares as Kufr) the Saying of Sayyid Qutb That Islam Is a Mixture of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http://www.themadkhalis.com/md/articles/bguiq-shaykh-ibn-jibreen-making-takfir-upon-the-saying-of-sayyid-qutb-that-islam-is-a-mixture-of-communism-and-christianity.cfm。
[30] Damon Linker, “The Marxist Roots of Islamic Extremism,” The Week, March 25, 2016, http://theweek.com/articles/614207/marxist-roots-islamic-extremism.
[31] Chuck Morse, Islamo-Communism: The Communist Connection to Islamic Terrorism (City Metro Enterprises, 2013), Introduction.
[32] Antero Leitzinger, “The Roots of Islamic Terrorism,” The Eurasian Politician, No. 5 (April-September 2002), http://users.jyu.fi/~aphamala/pe/issue5/roots.htm.
[33]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21.
[34] Dawn Perlmutter, Investigating Religious Terrorism and Ritualistic Crimes (New York: CRC Press, 2004), 104.
[35]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72, https://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911Report.pdf.
[36] Michael Scheuer,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 Osama bin Laden, Radical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2nd ed.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2006), 114.
[37]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38] Lawrence Wright, “The Man Behind Bin Laden: How an Egyptian Doctor Became a Master of Terror,”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6, 2002,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2/09/16/the-man-behind-bin-laden.
[39] Lawrence Wright, The Terror Years: From Al-Qaeda to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6), 17.
[40]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41]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XXIV, No. 3 (Fall 2017), 70.
[42]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 John Arquilla,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88.
[43]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3 (Fall 2017), 85.
[44] Anthony Bubalo and Greg Feal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slamism, the Middle East, and Indonesia,”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No. 9 (Oct. 2005):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20051101bubalo_fealy.pdf.
[45] Robert Manne, “Sayyid Qutb: Father of Salafi Jihadism, Forerunner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ABC, November 7, 2016, http://www.abc.net.au/religion/articles/2016/11/07/4570251.htm.
[46]Joshua Sinai, “Mining the Roots of the ‘Why and How’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31,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oct/31/book-review-the-mind-of-the-islamic-state-by-rober/.
[47]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 2014), 64-6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600/RR637/RAND_RR637.pdf.
[48]2011 Report on Terrorism,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14, https://fas.org/irp/threat/nctc2011.pdf.
[49]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41.htm.
[50]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13, 201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98_1_1.pdf.
[51] 时延春:〈周恩来与中东〉,《党史纵横》,2006年第一期,页7-8, http://waas.cssn.cn/webpic/web/waas/upload/2011/06/d20110602193952375.pdf。
[52] “U.S. Orders Closure of Palestine Information Office – Department Statement, September 15, 1987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98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08192756/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79/is_n2128_v87/ai_6198831/.
[53] Andrea L. Stanton, Edward Ramsamy, Carolyn M. Elliott, Peter J. Seybolt, eds.,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Africa: An Encyclopedia, Vol. 1 (Los Angeles: SAGE, 2012), 274.
[54]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
[55]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36.
[56] S. Fr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9.
[57] John Hooper, “Claims that China Paid Bin Laden to See Cruise Missiles,” The Guardian, October 20, 20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oct/20/china.afghanistan.
[58] Ted Galen Carpenter, “Terrorist Sponsors: Saudi Arabia, Pakistan, China,” The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6, 2001,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errorist-sponsors-saudi-arabia-pakistan-china.
[59] “China’s Role in Osama bin Laden’s ‘Holy War’ On America,”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3, No. 23, https://www.pop.org/chinas-role-in-osama-bin-ladens-holy-war-on-america/.
[60] Yitzhak Shichor, “The Great Wall of Steel Military and Strategy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 S. Frederick Starr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8.
[61] John O. Edwards, “China’s Military Planners Took Credit for 9/11,” NewsMax, September 24, 2002, https://rense.com/general29/sdspl.htm.
[62] “Chinese Firms Helping Put Phone System in Kabul,”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8, 200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1/sep/28/20010928-025638-7645r/.
[63] D. J. McGuire, “How Communist China Supports Anti-U.S. Terroris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15, 2005,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33.html.
[64]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5] 同上。
[66] “Ward Churchill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1835.
[67]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8] “Nicholas De Genova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2189.
[69]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70] 同上。
[71] 同上。
[72] “Lynne Stewart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861.
[73] David Horowitz, 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4), 37.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8/4/n106147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