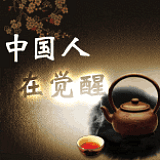在1989年六四凌晨,许多人目击了这样一幕惨剧:一辆疯狂的坦克,冲向刚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的学生队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带碾压得血肉模糊;死里逃生者,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辆该诅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伤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死了9人,有说死了11人,至于伤者,更是众说纷纭。这都不足为据。当局不公布死伤名单,别人说了,哪怕说得基本符合事实,也会当做“谣言”来追查。因此,必须拿出实证材料,让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来说话。
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这辆坦克碾死、碾伤的受害者作为寻访的重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寻找到的是:死者5人,伤者9人,一共14人。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其中10人已确知他们的籍贯和家庭地址。他们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来自江苏、湖北、安徽、陕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其中,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所大学的死伤人数就达6人之多。至于这一惨案中确切的死、伤数字,我想只能等待以后的时日来回答了。
现在,让我们忍着悲痛把思绪拉回到89年6月4日的凌晨,看看这群青年男女在那辆疯狂的坦克袭来时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吧。
林仁富,遇难时30岁,已婚,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博士生。3日晚,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4日凌晨,当戒严部队命令学生撤出广场时,两人遂推着自行车沿西长安街向六部口走去。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当那辆坦克向他们袭来时,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坦克会从人群中碾压过去。可就在这刹那间,林顿时成了坦克履带下的冤死者。他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他并没有任何反抗,而且是按戒严部队的“命令”撤离广场的。林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这里原是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上有三兄一姐。林家众多子女中他是唯一进入高等学府的,遇难时即将取得博士学位,且已联系好于当年10月赴日深造。林在他的同龄人中本来是个幸运儿,他是林家的骄傲和希望,却在顷刻之间化成了灰烬。一位优秀青年,遭此厄运,世人扼腕;然而,在强权者的高压底下,人们唯有叹息而已。
董晓军,遇难时20岁,生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学生,两年前他刚从江苏北部的一个小县城考入北京。父母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深爱着自己的父母。6月4日凌晨,董随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撤离时,走在队伍的尾部。他也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那辆疯狂的坦克碾死的,尸体被碾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状。儿子死了,父母把骨灰抱回江苏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门前小溪对面的岸边。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梦幻,唯有那由母亲的泪水汇成的溪流年复一年地呜咽着,控诉着那场惨无人道的杀戮。
王培文,遇难时21岁,生前与董晓军同属一所大学,且同属一个年级。老家在陕西省咸阳市。6月4日凌晨,王与董同时撤离天安门广场。董在排尾,王则在排头。他也被那辆疯狂的坦克轧死,尸骨粉碎。90年代初,我曾按友人提供的地址给死者亲属写过一封信,也曾向他们转达过来自海外留学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终没有收到对方的回信。以后我又曾做过努力,但没有结果。我想,这多半是出于恐惧吧。
田道民,遇难时22岁,湖北石首市人,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6月4日凌晨,在六部口被毒瓦斯熏倒在地,随后被开过来的坦克碾掉了左边的半个脸,其中一只眼睛完全被碾掉。当时被送往北京市急救中心,但已无法救治,当即死亡。田的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有兄弟姐妹8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学,他是这个家庭的唯一希望。田死后其家属把他的骨灰从北京抱回家乡——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安葬,父母至今一提起死去的儿子仍痛苦万分。
龚纪芳,女,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本科生,内蒙包头市人。6月4日凌晨,她随学生队伍撤离天安门广场,至六部口,遇坦克施放毒瓦斯,仓皇躲避时臂部中弹倒地,而且中的是“炸子”。她被送北京市急救中心,终因抢救无效身亡。她虽不是直接被坦克碾死的,但如果不是因为那辆坦克施放了毒瓦斯,也许她还不至于死于非命。
下面是伤者: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应届毕业本科生。4日凌晨,他随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至六部口时,正遇上那辆狂奔的坦克猛冲过来。当他发现坦克正向着身旁的一位女同学碾去时,便立即猛力把这位女同学推到了人行道上,可他自己却已躲避不及,倒在了坦克的履带之下,且被坦克拖了很长一段路程,以致昏死过去。他被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为保住性命,不得不锯去双腿,从此成为残废,终生与轮椅、双拐为伴。然而,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方在治伤期间,学校当局仍不放过他,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且不给他分配工作。方凭着他不屈的意志,在亲友的帮助下,去遥远的海南自谋生路。岁月对他来说是艰难的,但他不甘于成为生活的弱者,始终不息地向厄运挑战。由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
王宽宝,北京科技大学(原钢铁学院)硕士生。6月4日凌晨,随天安门学生队伍撤离至六部口时,与林仁富推车走在自行车道上,那辆疯狂的坦克碾压过来时,林当场轧死,王骨盆碾碎,送宣武医院救治,连续一周处在病危之中。在最初的几年里,医院为他做过多次大手术,伤口却迟迟不能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手术。他曾给我看过受伤的部位,不忍目睹,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但他同样有着不屈的意志,终于学有所成。
在这场由那辆疯狂坦克造成的血案中,死伤者最多的是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除两人被碾死,还有四位被碾伤。他们是: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有的被碾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此外还有两位伤者:一位名叫权锡平,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他在躲避坦克时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腿大动脉及坐骨神经分支被打断,现右腿呈萎缩状态。
另一位名叫刘华,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他与方政同时被坦克碾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后截肢。
这里还应该提到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女学生。6月4日凌晨,她参加了民众自发组成的一个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一带抢救伤员。可是,那辆发了疯的坦克竟丧心病狂地压向了这位善良的女学生,把她的一条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可是,开坦克的人难道也不长眼睛吗!连一个救死扶伤的女孩子都不放过,天下还有比这更惨无人道的吗!
我常常想,在战争年代两军交战时,对敌方缴械的士兵尚且还得放他一条生路,为什么对那些已经按命令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却不能放过!何况他们都手无寸铁,何况他们在撤退时没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时期竟如此残忍地滥杀无辜,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辆疯狂的坦克一样,已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疯子。人们难道能期望疯子做出合乎人类理性的事情吗!
多少年来,我总想弄清楚这辆坦克所属的部队,弄清楚这支部队的现场指挥员。几年前,我得到了那辆疯狂坦克的番号,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转移存放在家里的资料时,竟把当时记录下这个番号的一张纸片丢了。我期望有那么一天,那辆坦克能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那场血案的罪证。
补遗:这篇《实录》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那是有关上面这些死难者的父母和亲属的。一场劫难过后,留给他(她)们的是那无尽的苦难。
林家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底层,盼着儿子学成之后来改善全家的境遇,可一夜之间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林仁富的父母一直在贫困中受煎熬,人们很难想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林家还买不起一台彩电。前些年林母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我,她终于用转给她的人道捐款买了一台19寸的彩电,两位老人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了。我听了这话却无法高兴起来,心里只有一种苦涩味儿。林母是个不识字的妇女,起先收到捐款后都由别人代为签收。后来接受我的建议,终于练习着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我每次收到她寄回的收据,总会想到她的儿子。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写字的老妇人,如果她的儿子在,还用得着再学吗?两年多前,八十多岁的林父终因熬不过病魔的折磨离开了人世,临终时嘴里还念叨着:“我找仁富去了!”这时,他的话只有老伴才听得明白了。
由于林母她很早就参加了难属群体的联署活动,由于她常常往北京或无锡给我打电话,她居然受到当地安全部门的威吓和警告。但她始终没有在当局的淫威下屈服。她的回答很干脆:“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问你们,我好好一个儿子是怎么死的?”来人诈唬她:“你是不是又收到北京的信了?是不是丁子霖又给你寄钱来了?”她还是那样干脆地回答:“谁为我讨回公道,我就跟谁在一起!”每年的敏感时期,她知道我常常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监控,就常常来电话给我撑腰。她的福建口音我很难听懂,但我知道她这是在安慰我。我和这位老母亲以姐妹相称,如今已是多年了。
我与董家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后来,董的父母来信告诉我,当地的公安警察找到了他们门上,警告他们不准再与北京方面联系。为了不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精神上的困扰,我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然而我却总是放心不下。我一直想去探望他们,因为无锡与苏北董家仅一江之隔,路程不远。但我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1997年的秋天,正好有一位北京的难友去无锡我的寓所小住,我就讬他在返京途中前去探望。不久,那位难友给我带来了他与董的家人的合影。我这才知道,董晓军的祖父还健在,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但从他脸上那深深的印痕,不难想见他孙儿的死给他带来的打击。
(看中国: http://kzg.io/gb45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