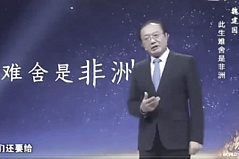这是一起父母双双自杀的悲剧,发生在文革那个荒唐的年代。
1953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区成立,劳布藏的父亲当了区长。劳布藏带20多户人家,在海宴县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一年后,他们又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团结社,劳布藏当社长。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被召去开会,扣留下来。部落里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劳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
劳布藏的父亲也被逮捕了。上级也不让他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那是黑人黑话,不能说。劳布藏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他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他们赶着牛马和羊走,有马也不许骑,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干部们很凶,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一句话,人不如牲口,他们不在人的数字里。
劳布藏回忆说,“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家乡‘嗷尔嗷尔’叫,眼里淌着泪。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悄悄地哭,没人敢大声哭啊。
到了托莱,除了一顶空荡荡的帐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还要再垒一个羊圈。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咋办?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族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干部们天天宣传:“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帐子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赶过来赶过去折腾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儿寡女。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然后用车拉走。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沉到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鞋。
1958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啊!冈察、祁连、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但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被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用绳子捆住打。他们在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石头,然后又吊在帐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灌辣椒、姜粉,我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看见父亲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却不见人。我们找了好多天,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时河面已经结冰了,天越来越冷,冰越结越厚。到第二年开春,冰层化掉,我才在河水边找到父母的尸体,他俩是用绳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30/n140637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