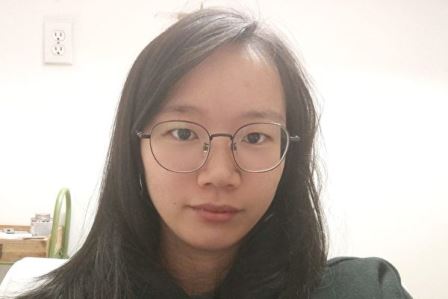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生活。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我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我对这个5000年历史的文化故土有很深的迷恋。
很多中国人分不清中共和中国的概念,他们以为爱国就是爱党,贬低中共就是贬低中国。我不怪他们,这种人长期生活在中共的宣传洗脑下,他们混淆了爱国和爱党的概念。这正是中共的阴谋,把政党和国家混淆在一起,当你抨击中共的时候,会有“爱国者”来攻击你,说你生养在中国,却抨击自己的国家。
近五年来,中国网络上关于“润”(Runxue, runology, and run philosophy are internet memes origin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referring to the study of how to leave China and immigrate to developed countries.)的话题甚嚣尘上。侧面反映中国的经济在下行。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该戏剧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Nora)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像我一样的Nora。
很多人想润,却“贫贱不能移”。美国签证对于中国人的拒签率是很高的。根据一项数据表示,2021年,中国公民申请美签拒签率高达79%,世界所有国家拒签率第二(除朝鲜100%拒签外),超过巴勒斯坦,伊朗,古巴,俄罗斯等美国传统敌国。 只有吉布提88%拒签率高于中国。
于是产生了很多“走线”的偷渡者,从香港或者澳门出发去南美洲,然后一路穿梭在热带雨林,走到墨西哥然后进入美国。这些“走线”偷渡者在中国国内是丑闻,在社交媒体是不能发的,中国执政者自我感觉良好,大国自居,战狼外交,民粹主义盛行。然和自居天朝上国,自己的人民却整天想着离开国家,去别的国家生存。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我从前一直对中国抱有幻想。认为15亿人口大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打破百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中国在过去40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确实飞速增长。但是,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努力,不是中共的执政能力体现。中共从1949年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以来,做错了很多事,唯一正确的就是改革开放。现如今又有开历史倒车的迹象:和独裁者普京合作,加大言论自由的管控,战狼外交政策,教育国内民众与西方国家为敌,民粹主义盛行。
来纽约之前,我在中国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我based在福建厦门,这个小岛与台湾面对面,隔着台湾海峡。我的同事都是福建人,按理说对台湾应该是手足连襟的兄弟姐妹情。但是在中共的战狼外交政策洗脑下,我的同事们都支持武统台湾。
记得去年八月,习近平下令在福建增设兵力,厦门岛突然出现了很多坦克。我身边的同事个个气焰高昂,扬言“打台湾”。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没有让国内的民众反思战争,反而高涨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是错误的,应该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
去年十月份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芝加哥和洛杉矶一趟,参展和拜访客户。当时中国还坚持新冠清零政策,境外回国需要在香港隔离3天,在中国境内隔离14天。
在香港的隔离是自由的,基本上可以自由活动。但是飞往中国隔离14天的经历是非常绝望和痛苦的。
我们是在天津隔离,因为其它城市的机票临时买不到。总共隔离14天,费用3500人民币。
落地天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我们已经在香港做了2次核酸检测,落地还需要再次检测。
三百多人的飞机,核酸检测效率慢,总共花费2小时。晚上六点多,冬天的天津已经天黑了。
我们的行李和人是分开的,行李被拉到单独的空间全部大消毒一遍。
我们排队等候大巴车接我们去2小时车程以外的隔离酒店检测。期间,等车花了1个小时。
大巴来了,一辆坐50人,一共6辆大巴。
当时我看到大巴车司机全副武装,穿着很厚重的防护服,又近视度数高,戴着很厚的眼镜,除此之外还要再戴一层防病毒的护目镜。我想起上个月(9月19日)发生在西南城市贵州的大巴翻车事件。同样的大巴车,同样的黑夜,我潜意识感受到危险,不想上这辆“死亡大巴”。
于是我跟工作人员联系,说能不能让司机摘掉护目镜和防护服,他本来高度近视,又全副武装的,又是黑夜,很难看清楚道路,万一翻车了,后果很严重。
完全合理的要求。而且考虑到上个月发生的贵州大巴翻车事件,我以为他们应该理解我,采取更有效的行动。但是贵州大巴车没有让他们吸取教训,继续延续这种不合理的,有巨大安全隐患的政策。
他们拒绝我的要求,还嘲笑我年纪轻轻这么怕死。他们不顾我的反对,把我的行李箱塞到大巴车内,把我赶上车。我当着全车乘客的面,说贵州大巴事件的严重性,也有人附和我。但是他们不够坚定,工作人员也不松口,说他们只是执行者,无法改变上级的命令。
我说如果这辆车出事,谁来承担责任?他不说。
无奈之下,我说我无法上这辆车,请让我下车。他们想直接无视我的需求,所以想直接开走。
我说如果你们拒绝我就直接从车窗跳下去。他们才放我下车。
我和行李都下车了,寒风中等他们的解决方案。其他人跟着车走了。
这时他们叫来了警察,来了十多个警察,围着我。他们都戴口罩,穿防护服,怕我传染病毒给他们。我说了我的合理诉求,要么白天转运到隔离点要么司机不能全副武装。他们无视我的需求,说办不到,并且一边说一边手机录影我。
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已经九点多了。他们叫了辆救护车把我拉去就近的空港医院。到了那边,我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站着等。因为他们没有预知我的到来,所以不知所措。
里面的人打了好多电话,终于让我进去,但是我的行李只能放在门口。在一楼的一间病房里,没有床,只有一个椅子,一台仪器。他们让我等通知。
半个小时后,等来了一通电话,是自称是天津卫健委的主任,她问我有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我说我没有病。她问那家庭有没有任何精神病史,我说没有。她说需要安排人给我做精神鉴定,我依然坚持说自己没有病。
她问我为何反抗防疫规定?我说我不想发生贵州大巴那样的事情,她说不会的,我想太多了,那个只是意外?我说谁知道意外会不会发生呢?她说理解我的恐惧。然后继续问我是不是精神上有受过什么迫害?
这个对话无法继续,我挂掉了。
后来他们说会派一辆救护车送我去隔离酒店。但是零下2摄氏度的冬天,没有暖气,他们的车一直没来。我就这样苦等,等到了第二天天亮。期间我要求要防寒的毛毯,他们说没有。
期间我去外面卫生间上厕所,他们派了一个护士专门盯着我,就在卫生间隔间外面看着我。
然后护送我回病房。
没有毛毯,没有水,没有吃的,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还是打算这样对我,我说我要饿死在这边了,求你们安排车子送我去酒店吧。
我主张了5次,才有一次回应。早上九点多他们叫了一辆救护车送我去隔离点。
中午十二点,我终于到了酒店。
在香港一起排队等飞机的一个女士在微信跟我说,因为我的反抗,他们工作人员跟那些乘客说我有精神问题,并且广为传播。
我和这位女士在香港机场排队等飞机的时候认识,她行李太多,叫我帮忙托运几件。因为在香港,我们是大陆人,备受歧视,行李超过一定量就要被收取高额的费用。
我们被安排到了面对面的酒店房间。
有一天夜里,她微信私信我说,她很饿,问我有没有食物。我说有,有巧克力和饼干。于是我把巧克力和饼干投掷在对方的门口。酒店内隔离的门一打开就会发生巨大的警报声。五分钟后,她打开门,也发出了巨大的警报声。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警察的男性问我昨晚有没有开门扔东西,我说有,并且解释了原因。警察说,这些他不管,重点是我违反了防疫政策。还警告我如果有下次,他要对我依法刑事拘留。
14天后,我回到了厦门,我工作的城市。在温水里泡着的青蛙很难知道自己即将走向死亡。这就是我出国以后再次回到厦门的感觉。我在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机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餐厅和酒吧开放,人们的生活回到正常。在中国大陆城市里,一切像是世界末日。机场一个人也没有,餐厅被贴上黄色的封条。从机场出来,打车回家,一路上没有任何车辆。
十一月,回到办公室后,我工作不如以前那么积极,总是坐在电脑面前发呆,需要别人大声叫我才能反应过来自己在走神。当时我以为是自己的问题,经过天津的隔离,周围人的质疑,我当时以为自己真的有某种精神疾病。
整个十一月我过得很恍惚。
十一月底,大量的白纸运动在大城市年轻人群中发生。我当时想发起在厦门的白纸运动。还没策划,好朋友就告诉我,在上海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因为参加白纸运动被捕入狱。
11月29日,我买了张机票来到美国纽约。谁也没告诉,办公室的咖啡杯还剩下一半咖啡。娜拉出走了。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1/n139633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