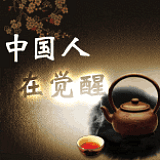近年来,由于脑控受害者的不断维权,被中共有意混淆、掩盖的“脑控”真相逐渐被揭开。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的一位高级职员披露了他被脑控的亲身经历,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用脑控(微波技术)实施迫害这一反人类的罪恶。
王先生曾是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体育部主任,2015年调往该集团下属的印务总公司做老总。他告诉大纪元记者,2016年开始,他遭到一种类似像幻听的“脑控”攻击。
在3年前的一段时间里,王先生突然发现他在接听电话时经常听到电话里有很多杂音,包括他远在美国的母亲打过来的电话都有这种刺耳的杂音。之后他就把通话声音录了下来,“我就听背景的声音,发现确实有人在跟我说话。”王先生说,从那时开始,无论他想什么,那个声音都会把他想的东西说出来,“而且我听得到的,别人听不到。”
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王先生说,这种没完没了的声音干扰令他非常痛苦,“我叫它语言暴力,如影子强盗一般如影随形,无所不在,而控制声音的人能洞察他人一切思维和想法,掌握他人所有的隐私和记忆,了解他人全部软肋和短处,并且,还处心积虑,精挑细选专门针对他人所有的要害之处,各种羞辱、训斥、讥讽、谩骂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地施以暴风骤雨般精确语言暴力打击我。”
王先生说,为了搞清楚自己听力是否出现状况,他透过在耳鼻喉科做专家的同学,对他自己的听力做了两次系统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他确实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比如在8000赫兹区域的听力达到15dB—10dB,我具有听力特异,也就是传统讲的特异功能。”
之后,王先生花了大量的时间才搞清楚他是受到了“脑控”的攻击,“脑控跟幻觉非常相似,”王先生说,刚开始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但我自己很清醒,不可能出现幻听,因为幻听总会有一些状态出现,但我没有,“他们就是故意营造幻听的状况让我去感受。”
王先生曾自己做了一些实验来证明自己是被“脑控”了,“我用印报纸的金属板将一个平方的房间的六面墙全贴上,我待在这个房间里发现,我想什么他们就读不出来了;我有时也测试他们,我想一个非常高的声音,结果他们唱不上去,把调降下来了,他们的声音是人唱的,而且我想的方言他们也读不出来。”
由于长期受到“脑控”的干扰,王先生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我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每天要考虑很多问题,但你要考虑问题几乎很难,在2018年干扰最严重的时候,人会极其烦躁,甚至发怒。”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先生还先后出过4次车祸,“有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开车,除非很短很短的距离,超过10分钟车程,我一定会睡着,这种睡觉不是完全沉睡,是似睡非睡,而且是不可抗拒地想睡。每次都是发生‘追尾’,只有一次是撞到屋檐,车子撞到竖起来了。”
王先生说,让他长期极度苦恼的问题是,由于“脑控”太过虚幻,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实其真实存在。以至于几乎无人认同“脑控”者,甚至根本都不认可其真实存在。
“我曾经尝试跟上级领导透露了一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最后就不说了,尤其在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不知道存在、完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最好不说,说得越多,也说不清楚,越抹越黑,对我越不利。”
谈到为什么会受到“脑控”,王先生怀疑这可能跟他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王先生的姐姐早年留学美国哈佛,之后曾是美国总统小布什科学家智囊团的成员,“这个智囊团有几十个人,她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中共安全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能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信息,被我拒绝了。”
王先生说,最初他的想法就是“他们拿我当试验品,了解具有听力特质的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或者对于他们盯上的人做这个实验,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最终是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想像的,到最后,慢慢受到他的影响,他们通过某种手段逼着你按照他们的路径在走,他们从中找到一些经验和手段。”
“就像当年日本的731,但他们把这个做到极致,到什么极致情况下会发生质变,或者某种情况下是底线。”王先生说,“他们想控制人,就采集人的大脑的数据,远程搜集、远程式控制,把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对于他们给我造成的这种痛苦,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死,你无法忍受。”
至于是谁在搞这个“脑控”实验,王先生曾怀疑或许是某一个团队买了一些高科技监听在干坏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团队干得了的事情,我有几次跟他们‘对话’,最早了解是总参2部、3部的情报部门在做这个事情。”
另外,王先生说,他中央的朋友反馈给他的信息是,“‘确实有脑控的事情,而且国家很重视,但不是我们国家搞的,是世界上很霸道的美国搞的,还说,我们苦于没有证据’。我知道肯定不是美国人搞的。他们是绝对不承认的,而且知道的人不会很多,即使公布出去它都不会承认,说你是瞎说,这个套路我在新闻界搞了多少年,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待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10/n115107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