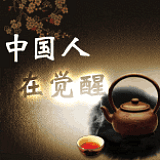1951年,31岁的巫宁坤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攻读博士。新年时,他忽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请他前去燕京任教。巫宁坤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归祖国。
当时,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劝他不要走,他不听,李政道就帮他打箱子。7月中旬,在登上邮轮前,巫宁坤问前来送行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一笑了之,二人话别。
1957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迎来事业最高峰。在大陆,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先后在监狱和农场被关押劳改近20年,九死一生。
1979年,“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国讲学,而巫宁坤进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此乃命运弄人?
“共产党你不要跟它讲道理,没有道理,……黑白永远是颠倒的。”巫宁坤的夫人李怡楷如是说。
1993年,巫宁坤在纽约以英语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记叙了自己从肃反到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经历。
中共在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创伤和灾难,被指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作为主要受难者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之后,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中共也不再允许来自党外的批评。巫宁坤的遭遇,确实是苦难海洋中的“一滴泪”。
“双百方针”与“阳谋”
1951年,中共在全国大学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被逼“改造”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改造”之后,又来了“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肃反运动再掀肃杀之气。几经打击,知识分子由此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料,到了1956年,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竟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松动。
1956年4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在当天的会议总结时说:“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5月26日,时任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郑重地向各界人士宣布此“双百方针”。陆还称,中共“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7月20日,陆定一对出席会议的中共各省市负责宣传、文教的官员们讲话,要他们听取批评,勿乱扣帽子:“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反领导等等。”“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
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只有500万知识分子。这500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500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在谈到“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造现在这种面貌。那么,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毛的讲话让很多原来对共产党存有戒心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与会的著名翻译家傅雷,事后给家人写信,表明自己当时的感动和对毛的钦佩。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在5月2日、3日、7日发表社论,进一步推动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在如此“诚恳”的邀请下,响应号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改进建议或表达不满。新闻界也大力跟进。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5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右倾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继续去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好处”。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撰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后又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12日印发党内。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式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做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驳斥,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
文章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在高等学校的校园里,鸣放更为激烈。从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陆续贴出几百张大字报,很多内容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用“北京大学民主墙”称呼做了报导。
在“鸣放”后期,各种意见都提了出来。共产党对于涌现的批评不能接受,例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储安平的反对“党天下”等观点。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
1957年6月14日,风向彻底变了。《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据说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反右”风暴
《九评共产党》中写道:“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中共出尔反尔,将实话实说、对党忠心耿耿的人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问题的通知》。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指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一倍,全国的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点名人数,也允许把右派骨干总数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当时,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因为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 反对“党天下”的意见,被称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右派,认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高度赞扬歌颂中共的费孝通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经赞成高校党委制,也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有1500位青年教师和学生在反右中被开除公职和学籍,发配到荒原大漠。20年后,1500人又全部被“平反”接回北京。
曾经因为毛泽东的讲话而心潮澎湃的傅雷,命运又如何呢?1957年,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的暴风骤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批判傅雷。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精神极度痛苦。
《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分子”的认罪书,还刊载了他们互相揭发的文章,这样既分解了“右派分子”,也从道德上摧垮了他们。
政治“帽子”一旦扣上,这些右派便沦为政治“贱民”,按照罪行的轻重被依次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受到前两类处罚的人员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大批右派相继死亡。那些所谓的“极右分子”,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被划成右派的人遭批斗打骂,受尽屈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
至1958年整个反右运动结束时,共有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分子,占500万知识分子的11%,受到牵连的达几百万人。1979年,中共“改正”了552,877名“右派”,发现整错者达99.98%,但是对96人决定“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5人,还有地方级91人。
“右派”血泪
在反右运动中,甘肃日报编辑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受到牵连,成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二人一同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在十工农场,王景超到了夹边沟,在那里活活饿死。
和凤鸣在回忆录中写:“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
当年头号学生右派、始终未得平反的林希翎说,当年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所以上当受骗,全是因为毛的号召。毛泽东让人们反对“三害”,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给党造成的极大的危害,说“你们应当帮助党整风,批判这些‘三害’,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讲得漂亮得不得了”。
云南昭通的李曰垓,13岁参加“革命”,16岁被划为“右派”,从1958年元旦过后到1978年底,李曰垓总共度过了20年零8个月的劳改岁月。李曰垓恢复自由后,在网路发表专集《噩梦醒了吗》。他写道:“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2007年6月6日至7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昔日的“右派”特地从中国大陆前往参加。
时年72岁的黄泽荣,笔名铁流,原《成都日报》记者。童工出身的他,15岁参加“革命”、追随共产党,是当年共青团系统三大右派之一,历经劳改23年。“划右”原因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他说,8800多字的作品,相当于为了写的每一个字,关了他一天。
黄泽荣说:“做右派的,都是讲真话,相信共产党的,有个人见解的。”他强调,下一代不能够再在“狼奶”中养大了,“现在对孩子就是不能够再接受这种谎话的教育,不能再吃狼奶。一定要在小时候就告诉他们历史,告诉中国发生了哪些事,什么叫反右斗争?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什么叫三反?什么叫五反?什么叫镇反?反胡风?”
黄泽荣表示,中国人至今还不敢讲真话,还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作为现在活下来的人,作为受害者,我们要把这个历史留下来,留给子孙,留给民族,留给世界,绝不让当局掩盖这个历史。”
时年74岁的任众说﹕“实际上我们对国家是负责任的,我们为国家提一提意见,能够早一点改进,国家更能够前进”,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全都成为“右派”和“阶级敌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参加会议的还有“右派”的后代,比如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黄炎培曾是中共大力统战的对象,利用他赢得知识分子的信赖。但是他的7个子女中,有5人被打成右派,其中两人被逼自杀。
与会的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余英时教授也做了发言。他说,中共第一次正式整知识人,是反右。“1949年(中共)一进了城,看你知识人就是次等人,或者是潜在的敌人。所以它绝对不会相信的,你怎么投降也没有用。它认为你口是心非,它认为你心没有交出来。所以后来一再要挖心,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2008年,一部四卷、120万字的《五七右派列传》问世,共有四百余篇、涉及1300多名右派的受迫害经历。作者申渊,本名陈愉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反右补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放逐内蒙古边疆劳动。
陈愉林说:他之所以要写右派历史,就是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共产党害怕的不是小骂它,它害怕的是说清真相。因为中共的政权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最怕人揭穿谎言。”
结语
著名学者胡平在《1957‧苦难的祭坛》指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诬陷直至剥夺人身权利和拘禁。”
王世三在《反右运动之一:引蛇出洞》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打断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脊梁,不仅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几乎丧失殆尽,而且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尊严也荡然无存。至今,‘反右’的阴影依然笼罩当下的中国,造成大陆知识分子难有担当,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犬儒主义者’及‘精致的利己者’。”
2006年的一个春日,林彪的长女林晓霖,致电其中学同学--反右时期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林告诉章,她从黑市上购得章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林晓霖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其实,她不必说“我们共产党”,不可把自己和中共混为一谈。因为在中共发动的整人运动中,中共欺骗了太多的民众,包括数千万共产党员,还有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受害者。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他的人生何尝不是一个中共治下的悲剧?中华儿女,是炎黄后人,不是马列子孙。远离中共、抛弃中共,不要继续把自己和共产党捆绑在一起,才是对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章诒和在《五十年无祭而祭》中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回顾昨日,我们理应深思--那一场灾难,引发的最大的悲剧,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让类似的悲剧,不断重演?我们必须谨记,必须清醒地面对,过去的岁月,留给今天和明天的警示。
参考资料:
1.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1991年, 九十年代杂志社。
2. 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2013年1月8日,大纪元新闻网,美国。
3.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一)”,2007年6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
4. 挥不去抹不掉《整风反右运动》50周年 (19),2007年6月,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7/11/n9379204.htm )